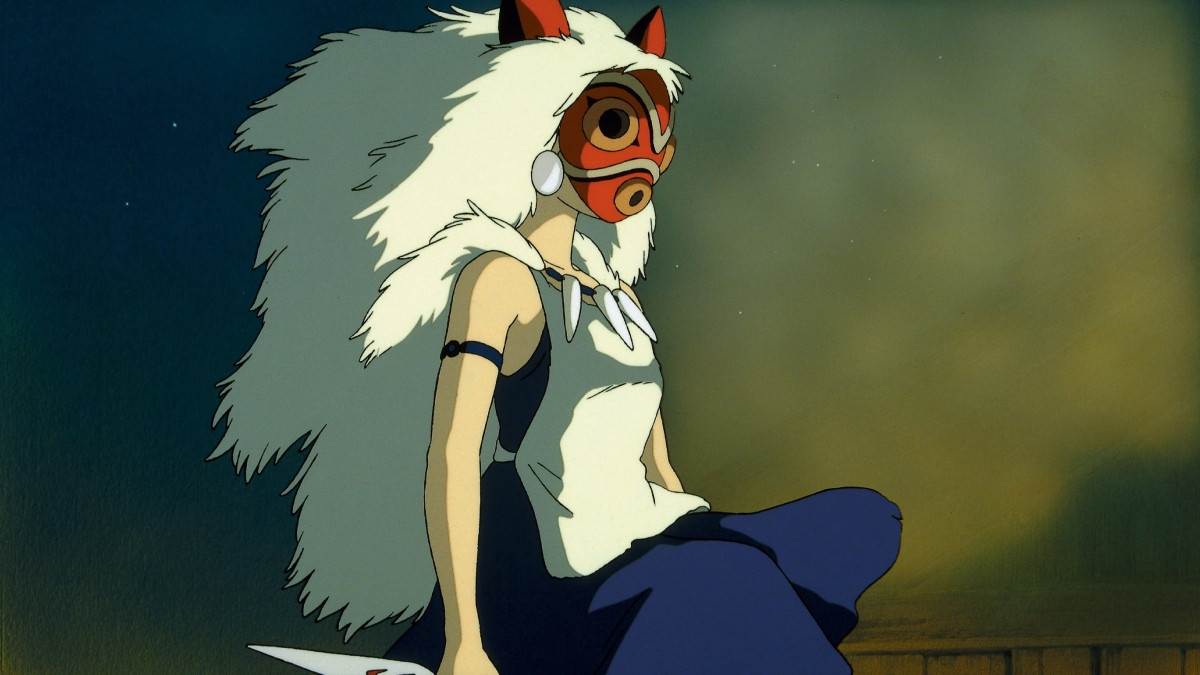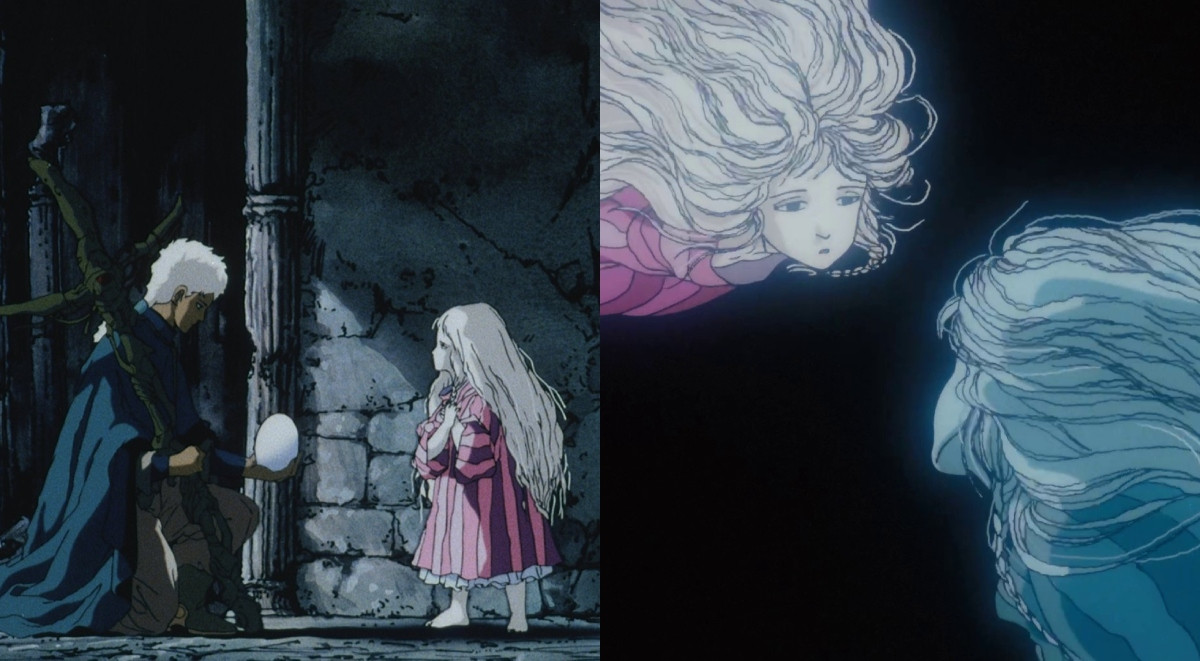坐擁書迷萬千、原作者石黑一雄親自監製電影《群山淡景》於2025年12月5日全台正式上映。集結廣瀨鈴、二階堂富美、吉田羊和童星鈴木碧櫻等魅力演員,本片挾第78屆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入選之勢,相繼亮相日本院線和金馬影展後,已然取得東西方不同歷史文化脈絡下的解讀與反響。La Vie專訪將撥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巨作光環,探知幕後製作祕辛,以及真正吸引導演選擇再次挑起改編大樑,「現在不談,以後要談就難了」的究竟何事。
1952、1980、2025⋯⋯時光流轉,哪怕濃墨褪去,淡筆仍保記憶中依稀可及之景。英國作家石黑一雄出道作《群山淡景(A Pale View of Hills)》自1980年代面世以來首度影像化,由日本導演石川慶(Ishikawa Kei)捕捉藏於深沉主旨背後的戲劇性乃至娛樂潛力,適切揉合洋氣與和風、新穎形式與古典神韻,從當代人漸漸無知亦無感的原爆事件和反核論述,轉而聚焦同樣占據原作相當份量的女性故事,進一步發散出如移民、多元與多樣性等21世紀你我依舊在面臨,也依舊能產生共鳴的議題。

欲藉此作搭起跨越40年時間鴻溝的橋樑,導演以自身所處「不近不遠」的時代位置,試圖領觀眾回望一段歷史,不,或許更該說是一份記憶——「我們在重現的是角色『記憶中的歷史』,而不是『歷史』本身。」然所有歷史某種程度上卻都經過「誰說了什麼樣的故事」堆疊建構,最終還是回到「記憶」這件事。因此,比起用宏觀的拍攝角度去看待史實中二戰引發的國族悲劇,石川慶改編石黑一雄小說,循的依舊是親子關係的微小架構,讓觀眾意念隨真相的隱蔽與揭露,跳轉於任何人事物皆具備的光與暗、希望與絕望等兩面性之間,冷不防勾動那些必須忘掉又忘不掉(只好扭曲成另一種形狀),或屬於個人、或屬於群體的巨大傷痛。
-
※ 以下訪談內容皆含有劇透,介意得知劇情情報的讀者,建議看過片後再行閱讀;若本身即為書迷,歡迎馬上進入《群山淡景》的電影時空。 ※
-
說一個關於長崎的故事
記憶會騙人
故事始於1980年代的英國鄉間,韓戰後改嫁英國人並攜女赴英的悅子(廣瀨鈴、吉田羊分飾青年和中年),在丈夫過世、與日本前夫所生的大女兒景子自殺後,決定賣掉一家人生活的房子;與英國丈夫所生的二女兒妮姬(Camilla Aiko飾)這才從倫敦回到老家幫母親一同收拾。幾日陌生相處中,她請求母親講述1950年代的長崎往事,關於佐知子(二階堂富美飾)及其女萬里子(鈴木碧櫻飾)的點滴於是被娓娓道來。可記憶會騙人、情感會讓現實偏色失真,這些往事終究只描繪出存在悅子心中的長崎。至於真實的長崎,對妮姬而言永遠都是不曾到過的地方。


妮姬視角相當於觀眾視角
電影透過將妮姬這個原作中相對被動的角色,強化為「發動者」的觀點轉換,成功為觀眾引路,使我們得以跟著無論內在養成、外在形象都不算距今太遙遠的人物,逐步發掘石黑一雄擅用的「不可靠的敘事者」筆法下,主角所說哪些是謊言,哪些可能是真相。而屋內一條象徵通往真相、末端是景子生前房間的關鍵走廊,特別借助狹長陰暗的場景設計,與當年佐知子的長崎住處做成圖像上的連結,「這個房子在電影中也是很重要的角色,我希望它本身如同生命體般存在。」深不著底的沉鬱氛圍彷彿景子孤魂不散,亦彷彿鑄成於長崎的「錯」緊抓不放。


色調切分時空,細節聯繫角色
1950年代長崎和1980年代英國色調一暖一冷,同時帶動視覺與觸覺體驗的「溫差」,不僅明確割裂夢與現實,更為長崎篇增添非寫實的奇幻感。掌鏡的是導演第四度合作的老朋友兼波蘭洛茲電影學院好同學Piotr Niemyjski。石川慶坦言,兩人通常不需要溝通到太細節的部分,也能理解彼此心中構想,「但我們還是會盡量保持充分的溝通。」舉凡個別場景要表達的重點是什麼、燈光和一鏡時長如何調控等,縱使尋求答案的過程往往很辛苦,也絕不放出鏡頭隨便就拍,「我們兩個都是這樣個性的人,一定會在找到理由後才去進行下一步動作。」



漫長而嚴謹的磨合造就堅實默契,應對此次分為日本和英國兩地的龐雜拍攝,「包括服裝、美術,甚至演員都大洗牌,感覺就好像同時間做了兩部電影。」然兩人合作無間下,幀幀影像展開真如兩副明信片套組,分別貫串英國篇和長崎篇的鏡頭美學耐人尋味,Piotr Niemyjski也憑此作提名BIFA英國獨立電影獎最佳攝影。

且若仔細去看,還能尋獲冥冥之中聯繫兩時空的彩蛋。比方說悅子英國家裡的掛畫,和長崎家裡的紙門擁有相同圖騰;又或者英國時期悅子的穿著,選用與長崎時期互有呼應的材質和花紋,皆是製作團隊精心鋪排的巧思。不過,講究各方面到位的背後,跨國取景也不會少被錢追著跑,「一開始預計拍10天,但有次製片跟我說『不如把1天改為準備日,先用9天排排看行程吧』。我想說有1天準備日的話也行,就那樣去排;結果後來大家都不叫那天準備日了,其實就是少了整整1天拍攝日。」導演略略苦笑地分享其一「趣聞」,表示在物價極高的英國,預算掌握確實艱難。

奔死還是重生?
原作和電影過半後,觀眾大都陸續意會到悅子口中的「我朋友」就是她自己。尤其電影特意安排廣瀨鈴飾演的悅子,從窗戶遠遠望見吉田羊飾演、如著喪服般全身黑的女人朝佐知子家走去,這「觀看真實自己」的一幕,更屬全片畫風變調的轉捩點。明示觀眾悅子即便深受喪女之痛所困,以至於需要編造故事並為自己設定一個旁觀角色來抽離痛苦,但到頭來,「我」仍得面對「她」——另一個自己、自己的另一面,才可能向原作者筆下不斷強調的未來前進。

而導演極為重視並著力刻畫的「兩面性」,除可見於悅子和佐知子身上、恐怖懸疑與靜謐美麗交織的氣氛裡,亦深刻彰顯在作品日文譯名《遠い山なみの光》承載的「光」字,「關於這個『光』,既是兩個女人在稻佐山瞭望台上談到的希望之光,同時也象徵原子彈落下的光,正負面是並存的。」有趣的是,整部電影大致上依時間序順拍至此,逐漸同步化的兩位演員、兩個角色,正按導演最初設定,於此瞭望台場景合為一體兩面。

再延伸論之,如果悅子在原爆中倖存可謂重生,為讓女兒隨自己移居英國的一連串作為又像帶她去奔死,生死的兩面性亦不言而喻。種種夾雜在原作曖昧語句間的思索和探問,經由較文字強烈且直觀的影像媒介,清晰展露兩面性、轉譯出雙重意涵,實為石川慶對《群山淡景》改編工作踩得相當有力的基調。


在他人期待與自身想望之間創作
坎城首映後收穫難忘笑容
那麼究竟找來原作者、世界著名小說家、自己也很會寫劇本的石黑一雄擔任監製,是什麼樣的體驗?石川慶表示,其實石黑一雄先生的態度自始至終保持「雖然這是我的原作,可一旦拍成電影,它就是你的電影,你可以用你的詮釋拍出你自己的電影」,以大體上不干涉太多、但適時提供意見的方式給足創作者信任感,甚至連年輕一輩必然拋不開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頭銜的顧慮,他都備好強心針:「《群山淡景》是我25歲很年輕時寫的出道作,你的經驗比當時的我還多,所以請有自信地去做。」時間就這麼來到坎城首映後,石黑一雄掛著滿臉笑容,「緊緊握住我的手說了句『非常好呢(すごく良かったよ)』」的最終回饋,令石川慶至今印象深刻。
驀然回首,已從新銳成為中流砥柱
2016年首部長片《愚行錄》即登世界三大影展、2023年憑《那個男人》橫掃「日本奧斯卡」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導演等8項大獎、2025年《群山淡景》勇闖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以及10年間還能解壓縮的豐碩創作歷程,石川慶從最早被冠上的「新銳」前綴,一路帶著常相合作的「石川組」成員們迎來愈趨壯大的作品規模,如今已然成為日本中生代電影導演裡中流砥柱般的存在。本人直言「滿不可思議的,我一直都覺得自己還是新人,回過神發現已經變成所謂『中堅導演』了(笑),最近特別有感。」
然廣受外界認可、逐步行穩文學改編之道、於國際影壇多有機會嶄露頭角⋯⋯這些「好的標籤」是否催生或反倒阻礙導演的未來創作?「(能參與大企劃當然是好事)但還是得在某些時候把尺度拉回來、縮小規模,有意識地建立一個能做更為個人化作品的環境。不然照這樣下去,企劃好像只會越來越大⋯⋯」雖未言明,話語間多少流露的不安,讓人確信導演肯定有許多有趣的念頭在腦中醞釀,「這次就已經拍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那下次的原作會是什麼簡直難以想像啊。」或許規格不見得往上加高,鍾情石川慶風格的觀眾們,想必非常期待導演在小製作裡大放異彩。

記憶終有一天只會剩下記錄
終戰80年,哪怕世上還有一名困於傷痛中的人活著,有些話就不能被說。然而,身處一個時代銜接下一個時代間轟隆作響的巨變期,如同本片以男人和女人二分的「與時代俱進」和「被時代拋下」群體,當今人們也嘗試解除噤聲,從歷史洪流中奮力將舊情感抓入新價值之中,不讓記憶太快流逝為記錄。
「現在我們還能把那個時代的事當成『記憶』訴說;但再過幾年,就只能作為『記錄』來論。到那時候,要冷靜對話可能就很難了。」專訪最後,忍不住問出那個抓緊褲腳擔憂會不會得罪不同信仰者的「當代日本怎麼談二戰」問題。不過是多慮了,接在帶著笑意的「怎麼說呢⋯⋯」之後一席話,導演並沒有不答,卻也輕巧地擴大問題核心,指涉日本以外、包括台灣在內的整個當代社會,皆可能面對的類似情境:過去的「對錯」難單面論斷,然認知與思維更新所致的「改變」並非壞事,異觀點尤需在來得及時好好對話。這無疑扣回1977年生的石川慶、在2025年拍出《群山淡景》的必然性,以及,作為時代連結的重要性。

日文表達連結的動詞「繋がる」語帶「羈絆」意味——《群山淡景》探討人事物的一體兩面,而情感恰恰塗刷了歷史高牆的兩面:但凡情感在,很多事情談不得;可不談,待現在仍懷情感的人慢慢逝去直到為數「零」,記憶便成「已死」的記錄,無以再生成對話空間。或許我們永遠不得而知何時最是時候,那麼趁記憶還能引起這些、那些波瀾⋯⋯(留予彼端的你自由填答)。

-
文|Ning Chi 口譯|陳幼雯 圖片提供|東昊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