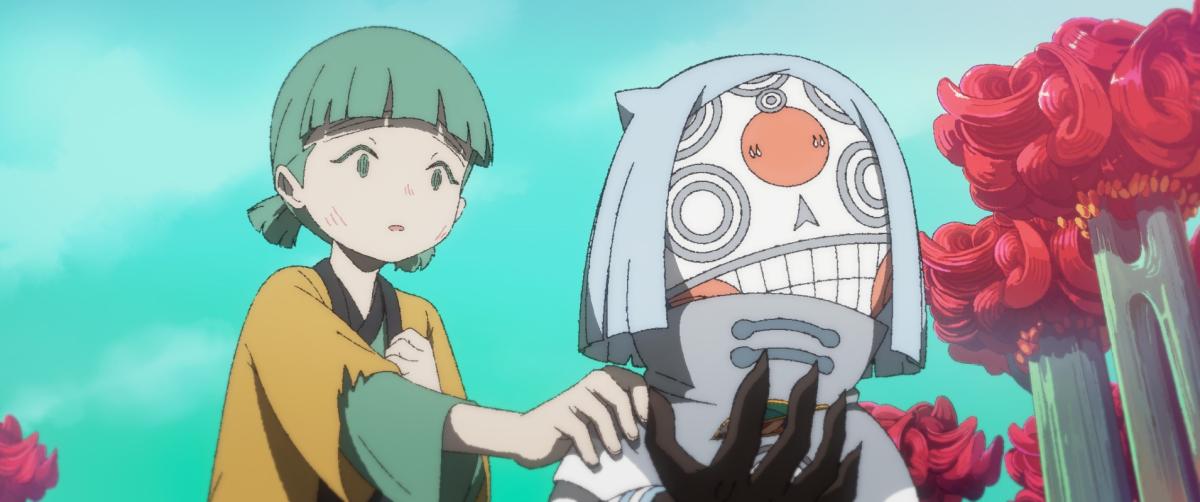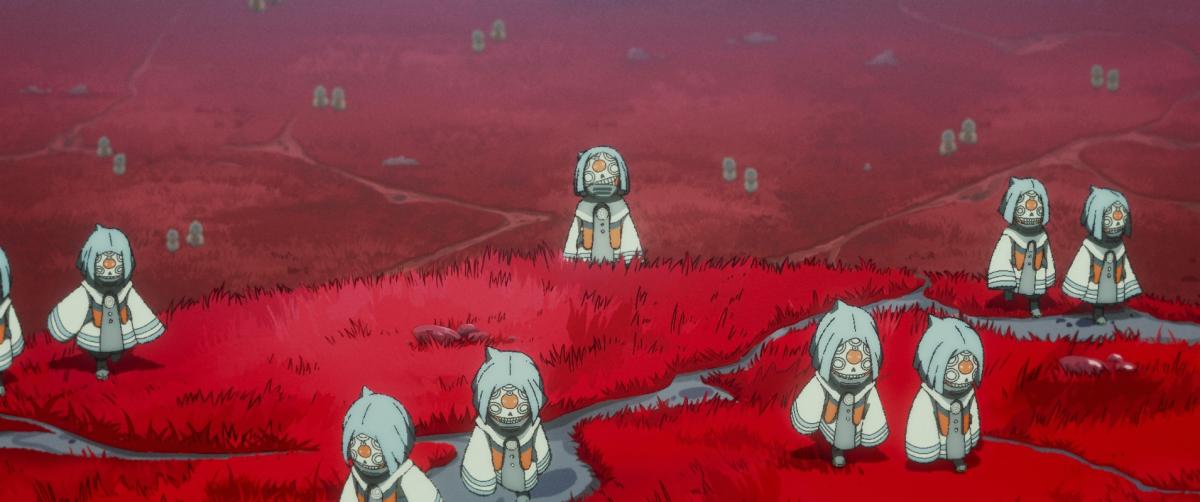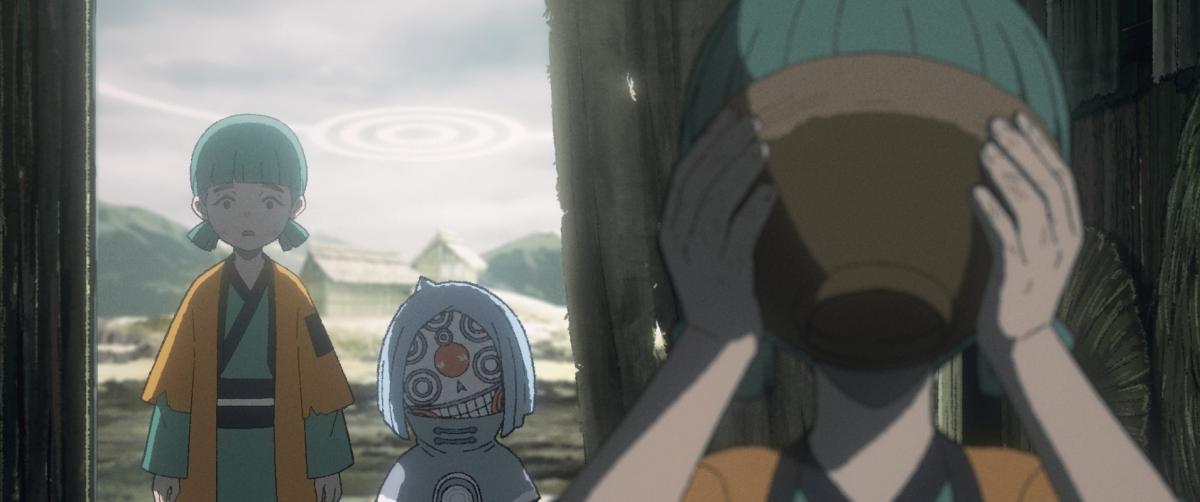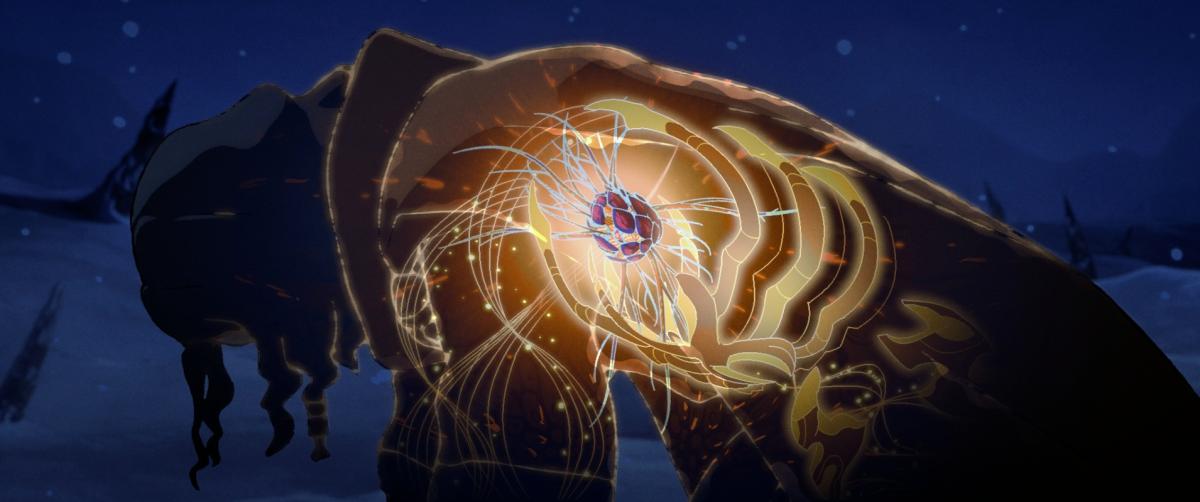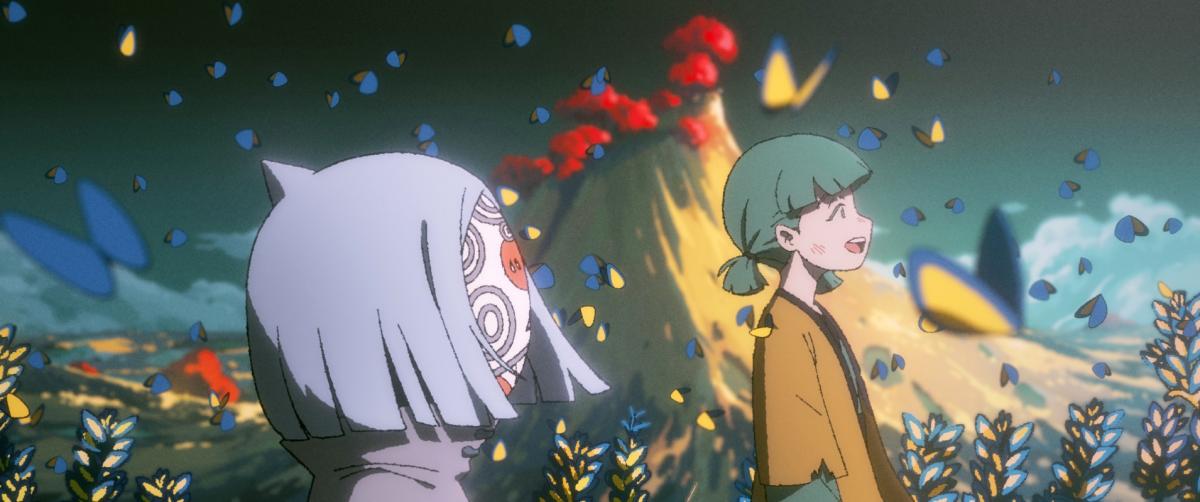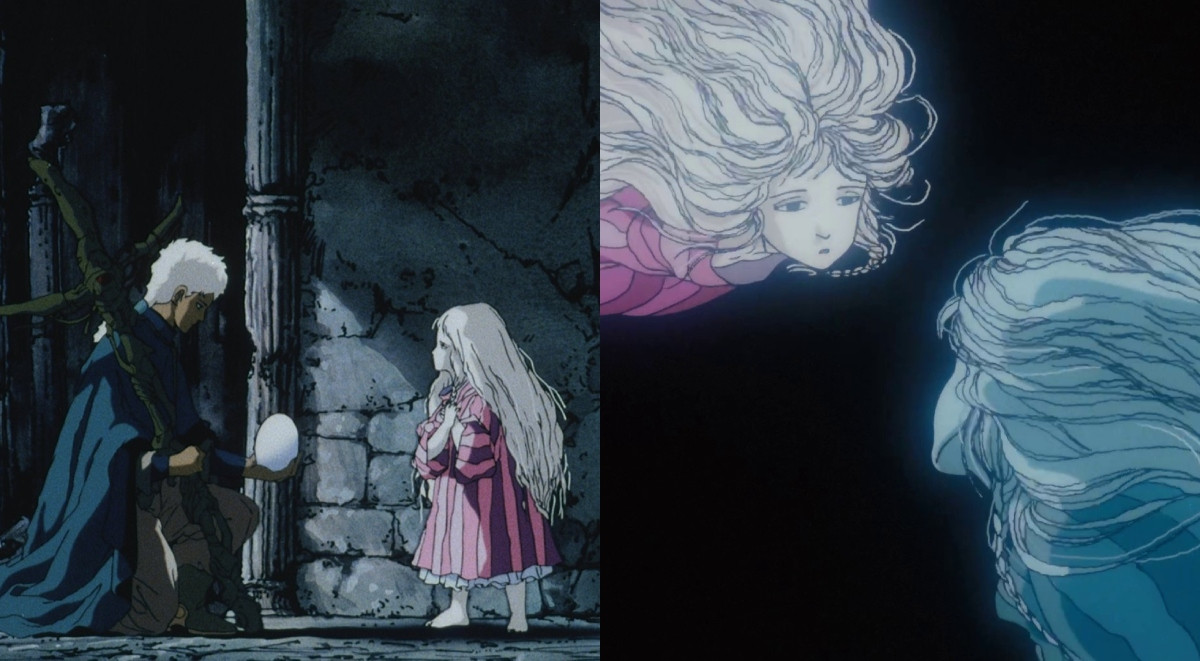現實世界發生的事,往往比虛構更震撼或動容。紀錄片有時正是發現或呈現這樣的事實,也有時是因為拍紀錄片才造就這樣的故事產生。以下精選7部紀錄片,帶你走進連編劇也不敢這樣編的神展開。注意!文章將會爆雷,若在意此觀影體驗者請小心服用;但紀錄片的迷人之處也在於,即便結果已知,中間的過程不會因此失色,甚至更想一探究竟。
《百事可樂,說好的戰鬥機呢?》
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法律攻防
1995年,百事可樂推出了一項行銷方案:只要購買百事可樂商品就能獲得積分,這些積分可以兌換各式各樣的贈品。電視廣告以學校為背景,展示了T-shirt、夾克、太陽眼鏡等贈品和所需點數,最後有架戰鬥機降臨,並打上戰鬥機需要的兌換點數是700萬點。這是開玩笑吧?當時20歲出頭的商學院學生約翰.倫納德(John Leonard)可不這麼想,因為廣告中沒有放上任何免責聲明。他找來富商陶德.霍夫曼(Todd Hoffman)作為贊助人,更發現百事可樂開放購買點數,10美元可以買到1點,於是寄了張70萬元的支票給百事可樂,要求兌換戰鬥機。
這部片是由4集組成的紀錄劇,雙方詳細的法庭攻防戰都在裡頭,中間更夾雜大公司的法律與媒體操作、百事可樂也並非頭一次誇大行銷,還有其他有心人士的介入,讓原本動機單純的約翰一度動搖。最後約翰的訴求遭法院駁回,但這場官司成為了法學院經典案例,他和陶德的友誼也持續至今。他是輸了,不過人生過程的價值判準本來就不是只有輸贏。
《伊卡洛斯》
以身試法竟牽扯上國際醜聞?
導演布萊恩.福格爾(Bryan Fogel )是位業餘自行車手,相當崇拜7度奪得環法自行車賽冠軍的藍斯.阿姆斯壯(Lance Armstrong),然而這位車神卻被爆出長期使用禁藥,發現原因並非藥檢,而是隊友檢舉。消息一出,布萊恩失望之餘,決心以身試法施打興奮劑來贏得自行車賽,並將此過程拍成紀錄片。聽聞這個挑釁又爭議的計畫,許多科學家紛紛拒絕,最後找到了俄羅斯科學家格里戈里.羅德琴科夫(Grigory Rodchenkov)協助。
《伊卡洛斯》前半部詳實記述怎麼施打禁藥、又怎麼逃過藥檢,卻在俄羅斯選手被世界反禁藥組織(WADA)指控服用禁藥後轉了一個大彎。原來格里戈里正是協助俄國政府施打興奮劑的關鍵人物,布萊恩先是助他逃亡美國,接著紀錄片就轉向揭露國際醜聞與躲避政治迫害的攻防。關於俄羅斯的興奮劑事件,現在爬梳網路都留下不少新聞,以及2020東京奧運俄羅斯以「ROC」(Russian Olympic Committee,俄羅斯奧委會)參賽,亦是國家因禁藥風波遭到禁賽的原因。
《我來自北韓 我想回平壤》
長達7年的歸北行動
罹患肝病的北韓主婦金蓮希,決定到中國尋求更好的醫療資源,卻因中國和北韓同為共產主義,誤以為中國也設有免費醫療制度,沒想到實際上看病拿藥樣樣都要錢。經濟窘困之下她開始到餐廳打工,聽聞掮客提及到南韓能更輕易賺錢,而這一踏上南韓,竟讓她意外成為「脫北者」。脫北者的故事就已足夠引人想一探究竟,但《我來自北韓 我想回平壤》的韓文片名直譯為「歸北者」,在好奇上又多了一層不解。
片中記錄下金蓮希7年間的歸北行動,首先尋求正當管道受阻,接著向越南大使館申請政治庇護、坐上冰球世界盃的北韓隊巴士、從事間諜活動⋯⋯,荒謬手段連發只為被驅逐遣返回國。她想歸北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先生和女兒都在北韓,就只是想與家人在一起。金蓮希不是感受不到南北韓的生活差異,但她說:「自由、物質生活和任何類型的其他誘因,都不比我的家人和故鄉來得重要。」不論脫北或歸北,生命的難題都不會因踏上他方而消解。
《大地蜜語》
歐洲最後一位女性養蜂人
巴爾幹半島深處山區,一座沒有道路、電力、自來水、農業基礎的荒廢村莊,住著歐洲最後一位女性養蜂人哈緹潔(Hatidze Muratova)。神話般的場景與角色,在世界的角落真實上演。《大地蜜語》不僅片中故事超脫凡常,片外也創下影史首次同時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和最佳國際影片的紀錄。哈緹潔與半盲的母親同住,維持徒手採蜜的方式,敲開峭壁上的碎石,坦露的整排蜂窩隨即竄出成群野蜂,但她不以為意,口中唸道「你一半,我一半」,徒手拿走半片蜂巢,相信必須留一些蜂蜜給野蜂,才不至於來攻擊蜂巢。
這樣的和諧卻在游牧民族遷移到隔壁而有了變動,鬧哄哄的7個孩子、無處放養的牲畜,為寧靜生活帶來生機。哈緹潔也親自教導採蜜,他們卻不依循「你一半,我一半」的法則,最後哈緹潔的蜂巢也因此被野蜂攻擊殆盡。之後游牧一家離開了,他們另覓居所,哈緹潔和母親依舊留住在此,望著冰天雪地,習慣嚴冬的她不知能否想像春天到來的時候。
《最酷的旅伴》
街頭藝術家遇上法國電影大師
相差55歲的大人物與小伙子,彼此從不對盤到忘年之交—這是許多劇情片都有過的設定,但《最酷的旅伴》這組拍檔又因兩位創作者現實的身分與作品,讓觀影層次不止於劇情發展與角色情感。當時33歲的街頭藝術家JR,與88歲的法國新浪潮電影運動代表人物安妮華達(Agnès Varda),兩位在路上絕對會擦肩而過的藝術家,決定一起展開藝術行動。兩人一同坐上攝影車,踏訪法國鄉村小鎮,與當地居民交流後為他們拍下肖像,大圖輸出後貼在公共建築牆面。
他們一路上聊天拌嘴,安妮華達總要JR摘下永不離身的墨鏡(當然每次都被拒絕),還到羅浮宮重現高達《法外之徒》的經典畫面,由JR推著坐在輪椅上的安妮華達盡情奔跑。旅途最後兩人真的去拜訪高達,卻遭高達留在家外的謎語吃了閉門羹,看著沮喪的安妮華達,JR決定為她拿下墨鏡,她看著他說:「雖然我看不清楚,但是我看見你了。」
《赤手登峰》
不靠繩索征服陡峭巨峰
這部片的英文片名「Free Solo」是一種攀岩類型,不使用任何繩索、吊帶等安全裝備,全憑攀岩者的意志與技巧登峰,只要失足,就極可能受到重傷或死亡。光是這項攀岩類型就已經令人難以置信,《赤手登峰》主角艾力克斯.霍諾德(Alex Honnold)更是要挑戰900多公尺高、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的「酋長岩」(El Capitan)。這樣充滿震撼奇險的人物與行為,很容易讓紀錄片變成在仰望一則奇觀,抑或獵奇式滿足感官,但《赤手登峰》把艾力克斯「為什麼非得攀登酋長岩」的心理狀態交代完整。不僅採集其成長與家庭背景,甚至以科學方式檢測腦部,發現他掌控恐懼感官的杏仁核發育停留在小孩階段;以及從原本隻身一人到遇上女友,挑戰酋長岩的渴望又更為複雜。從現今的「時空旅人」視角,可知艾力克斯的人安好健在,還和片中女友結婚生子,但目睹他攀上酋長岩的過程時,仍不禁緊張甚至不敢直視。觀影最怕爆雷,但這部紀錄片完美證明過程本身就足夠迷人。
《女畫家與偷畫賊》
畫家何以為竊賊作畫?
「她總是很認真地看著我,但卻忘了我也時刻觀察著她。」這個「她」,是女畫家芭博拉(Barbora Kysilkova),而說話的「我」,是偷了她的畫的竊賊卡爾貝提爾(Karl-Bertil Nordland)。不過這曖昧的話語,怎麼會從理當對立的兩個身分間產生?2016年,挪威奧斯陸「諾貝爾藝廊」有兩幅畫遭到盜竊,畫作均來自沒沒無聞的畫家芭博拉。這起在光天化日下犯案的手法無他,警方很快就依循監視錄影機逮捕偷畫賊卡爾貝提爾,當他被問及犯案動機,「因為它們太美了啊。」他說。這句話觸動了芭博拉,想為他畫下肖像畫。而當卡爾貝提爾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肖像畫時,忍不住哭了,因為從來沒有人這麼認真的凝視自己。《女畫家與偷畫賊》就記錄下兩人從失主與竊賊到畫家與模特兒,以及成為彼此理解的朋友的過程。這才慢慢知曉,看似迥異的兩人其實沒那麼不同,都在過往人生裡有過精神創傷與人際傷害。整部片的離奇發展與情緒堆疊,在結尾的一幅畫作裡達到高點。
文|張以潔 圖片提供|Netflix、海鵬影業、車庫娛樂、希望行銷/輝洪、Dis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