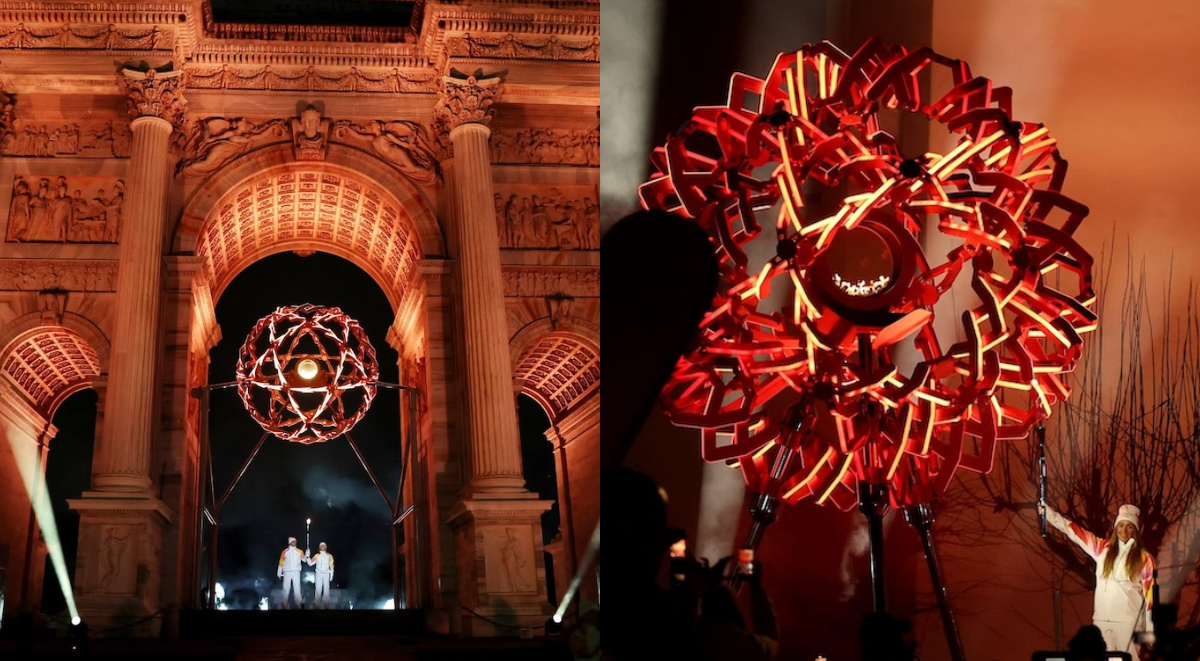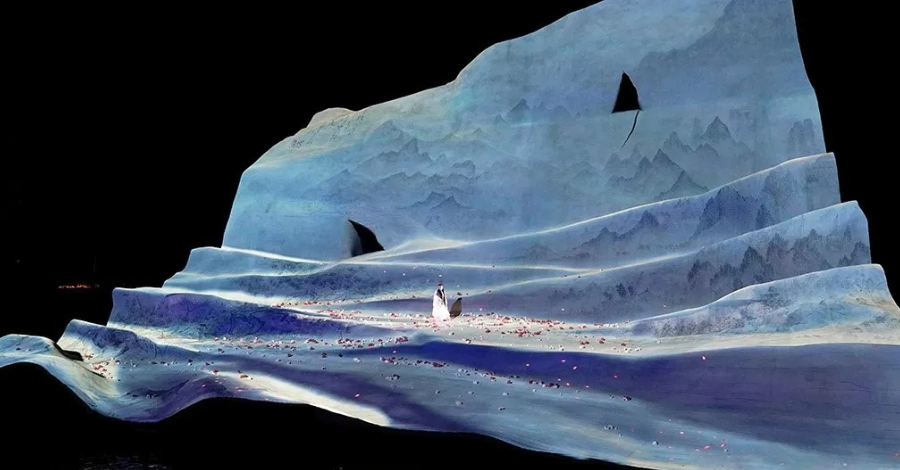藝術家佐伊.李歐納深具哀悼意味的傑出作品(獻給大衛的)「奇異果實」。奇異果實是裝置藝術,完成於一九九七年,現在是費城藝術博物館的固定館藏之一。作品由三百零二顆水果製成,包括柳橙、香蕉、葡萄柚、檸檬和酪梨,果肉已經吃光,剝下的果皮先曬乾,再用紅、白和黃線縫起,以拉鍊、扣子、皮筋、貼紙、塑膠、鐵絲和布料裝飾。完成作品偶爾會共同展出,偶爾則是一小群放在展覽館地板上展示,果皮毅然決然地繼續腐爛、縮水或發霉,直到變成灰燼,完全消失。
這件作品明顯是傳統的虛空藝術作品,描繪物質從新鮮到腐爛的過程,李歐納用「奇異果實」紀念摯友大衛.瓦納羅維奇。他們在一九八○年相識,兩人都在下班後市中心的新浪潮總部夜店Danceteria 工作,之後更雙雙成為愛滋行動聯盟的成員,有陣子參加同一個親和團體,意思是十幾年來他們一起創作,暢談藝術,參加抗議活動,然後一起被逮捕。
大衛在一九九二年過世,這個時候愛滋行動聯盟正好逐漸瓦解分裂,會員試圖讓根深蒂固的有害制度轉型,同時照顧與哀悼摯愛的朋友,在這雙重壓力下組織崩塌變形。很多人都選在那時離開,李歐納也是,她離開了紐約前往印度,接著再到淡季的普羅文斯敦待一陣子,然後才到阿拉斯加。奇異果實就是在她孤獨那幾年誕生的作品,若非呼應愛滋病盛行那些年的慘重死亡,就是對改變政治而做的努力感到疲乏。
一九九七年李歐納與她的藝術史學者朋友安娜.布魯姆(Anna Blume)進行的訪談中,講到第一個水果裝置藝術是如何誕生。
「這也算是一種自我縫合。剛開始時,我甚至沒想到我是在進行藝術創作:我受夠了浪費,受夠一直丟東西。有天早上我吃了兩顆柳橙,但就是不想丟果皮,所以就在無意識的狀況下把柳橙縫回去了。」
這件作品馬上讓人聯想到大衛用五花八門的媒材製成的拼貼作品,其中包括物件、相片、表演和電影場景。一大塊麵包被切成兩半,然後粗略地縫補起來,再以猩紅色的編織翻線填補兩塊麵包間的空間,有一張很有名的相片,是用他自己的臉,他的嘴唇緊密地縫合,針縫處畫上狀似鮮血的點,然後穿線。這些都是愛滋危機時期的經典作品,作品印證了沉默和忍耐、聲音遭到蒙蔽而孤寂的感受。有時候縫線似乎具有補償作用,但大多時候是讓人看見,並且引起眾人關注審查制度與隱藏的暴力,以及大衛世界裡無所不在的隔閡與迴避。
看得出水果在講同一場抗爭。作品名稱中的「水果」,用指男同志的粗俗俚語,他們是怪異的產品,社會的棄兒。名稱亦引用自比莉.哈樂黛講述凌遲的歌:歌詞描述恨意與歧視,以殘酷暴力的形式施加在身體上,焚燒到彎曲變形的人體被掛在樹上。比莉.哈樂黛為個人與制度上感受的寂寞發聲,她生於寂寞,死於寂寞,一生缺乏關愛,種族歧視讓她傷痕累累。曾有人直接對著比莉.哈樂黛喊她「黑鬼」,即使是在自己擔綱表演的場地,她也不得不被迫走後門。這樣的她,想用有害健康的酒精與海洛因為自己療傷。一九五九年夏天,比莉.哈樂黛在她位在西八十七街的房間裡吃著蛋奶凍和燕麥粥倒下,一開始她被送到尼克伯客醫院(Knickerbocker),之後轉到哈林區的大都會醫院,然後被丟在那裡—情況就跟後來幾年不少愛滋病患一樣,尤其是黑色或棕色皮膚的人—她被擱在走道上的輪床,說來也不過是另一件濫用毒品的病例。
不被當人看待和拒絕醫療,最可惡的是這種狀況也曾在一九三七年發生。當時有個陌生人打電話告訴她,她父親克拉倫斯死了,問她遺體該送往何處,那時血跡仍留在他的白色長襯衫上。
肺炎,她在她的自傳《哼著藍調的女伶》裡記錄:「害死他的不是肺癌,而是德州達拉斯。他四處奔走,從一個醫院跑到另一個,想要尋求協助,卻沒人肯幫他量體溫或收留他,這就是不爭的事實。」她唱著那首「奇異果實」,抗議父親的死,歌詞似乎「說出害死爸爸的一切」,隨後這一切也同樣害死她。她沒再走出大都會醫院,以藏有麻醉毒品的罪名遭逮,人生最後一個月都在醫院病房度過,由兩名警察監督,污名化的受害者所承受的羞辱毫無上限。
愛滋行動聯盟藉由他們採取的行動,想要引起大眾關注這些問題,解開和挑戰那些制度的公權力,他們讓某些族群的身體變得微不足道,例如同性戀、毒癮者、有色人種和流浪漢,彷彿他們死有餘辜。八○年代末,愛滋行動聯盟議員同意,他們應該把範圍擴張到男同志外,觸角要伸得更遠,讓大家看見其他族群的需求,像是吸毒者和女人,尤其是娼妓。
李歐納在愛滋行動聯盟口述歷史計畫的作品中,談到她的作品主要在探討針頭交換,在當時針頭交換是預防愛滋擴散的極端作法。雖然紐約市長郭德華執政時期曾短暫通融,但朱利安尼執政黨卻不能默許,於是針頭交換就跟在美國和世界各地一樣,變成非法行為。李歐納為癮君子成立了一個淨化和愛滋教育的案子,卻因此遭逮捕、控訴、審判,對注射器具持有法的合法性下戰帖,最終落得漫長的牢獄之災。
奇異果實是由不同的針線活集結而成的作品,這不是激進主義行動,也未參與抗議或刻意違法,不過依舊探討一樣的公權力問題。這個作品包容並靜靜守護排外、喪失與孤立的痛。這很政治,沒錯,但也很個人,再再說明她個人的經驗,也就是肉身不可避免遭逢的後果。沉默寡言的水果用它們的渺小,它們的特性傳達了分離之苦,消逝之痛,對已離去且永遠不可能回來的所愛的渴望。
即使轉譯至電腦螢幕,它們的懇求依然存留。看著它們變成縫合的柳橙,以絲線荒謬纏繞的香蕉—很難感覺不到情緒的拉扯,既是對傷害的回應,也是對修補不夠、殷勤執著修補、充滿希望的回應,一針一線,用扣子和拉鍊縫縫補補。
我不是唯一覺得這些水果讓人傷感的人。在《Frieze》藝術雜誌中,有篇關於佐伊.李歐納作品的一段獨白,評論家珍妮.索金也描述她在剛跨入千禧年之際,在費城藝術博物館心煩意亂地閒晃時,第一次看見這個裝置藝術品。「遠遠地看,」她寫道:「看起來就像垃圾,但當我更靠近一點時,我的煩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感到哀傷,瞬間覺得非常寂寞—絕望像貨車般撞上來,縫合的水果荒誕卻難以解釋地親密。」失去是寂寞的親友,這兩者交叉重疊,這樣一個哀悼的作品引發寂寞和分離感,想來也不意外。死亡很寂寞,肉體的存在本質上就很寂寞,被困在一個不斷邁向腐敗、縮水、消耗和破裂的身體。當然還有喪親的寂寞,失去或愛情破滅帶來的寂寞感,失去身邊重要的人的寂寞,哀悼的寂寞。
這一切都能透過死去的水果,丟在美術館地上乾掉的果皮表達述說。奇異果實之所以感人,之所以如此疼痛,是因為縫紉工活讓寂寞的另一面變得更澄澈:無止盡的痛苦盼望。寂寞是一種渴望,渴望親密、結合、參與、接合,渴望能將遭到切割、拋棄、破碎或棄置一旁的事物集中起來;寂寞是一種對整體、感覺完整的渴望。
【延伸閱讀】好書推薦《藝術的孤獨》:安迪沃荷、紐約與寂寞
☆本文摘錄自:
作者:大英圖書館駐館作家 奧莉維亞‧萊恩 Olivia Laing
給居住在孤寂城市中的你,和偶爾寂寞、獨特的所在,以及想要得到慰藉的心情。
謝哲青 ∣ 知名節目主持人、作家
吳洛纓 ∣ 金鐘編劇
曾文泉 ∣ 《喔,藝術,和藝術家們》
所在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