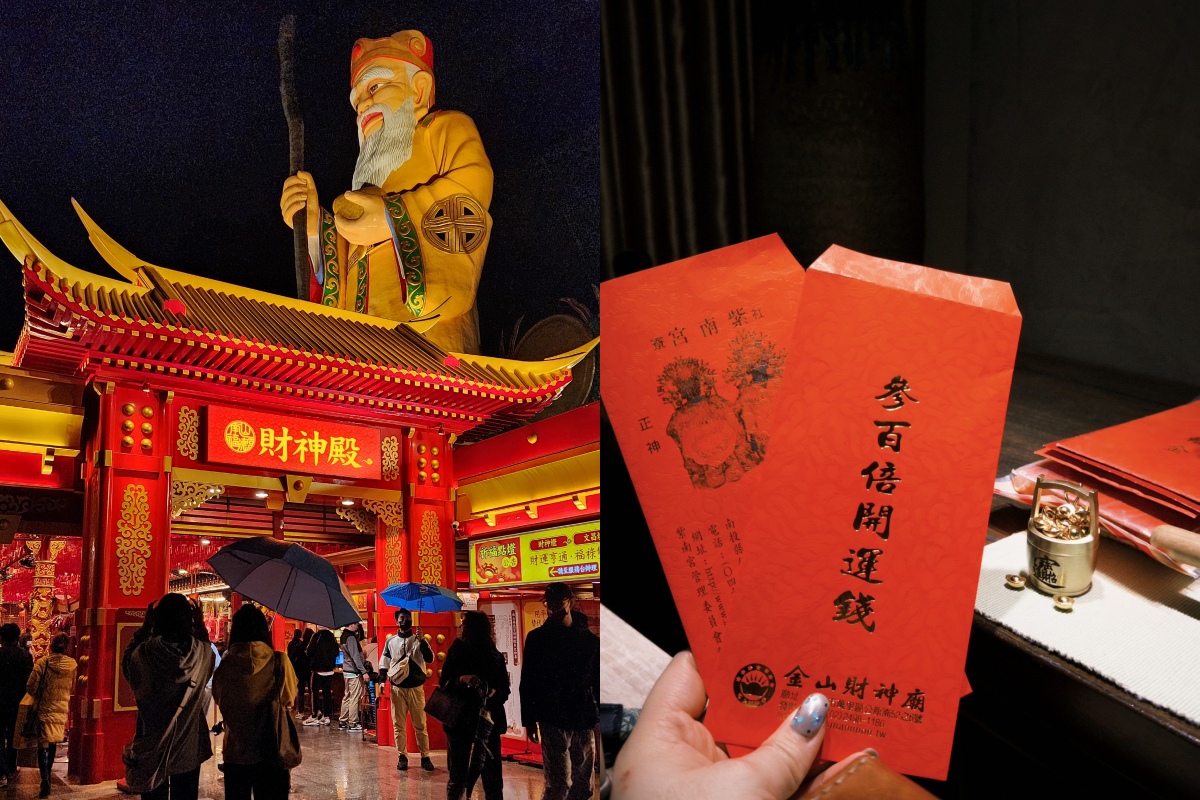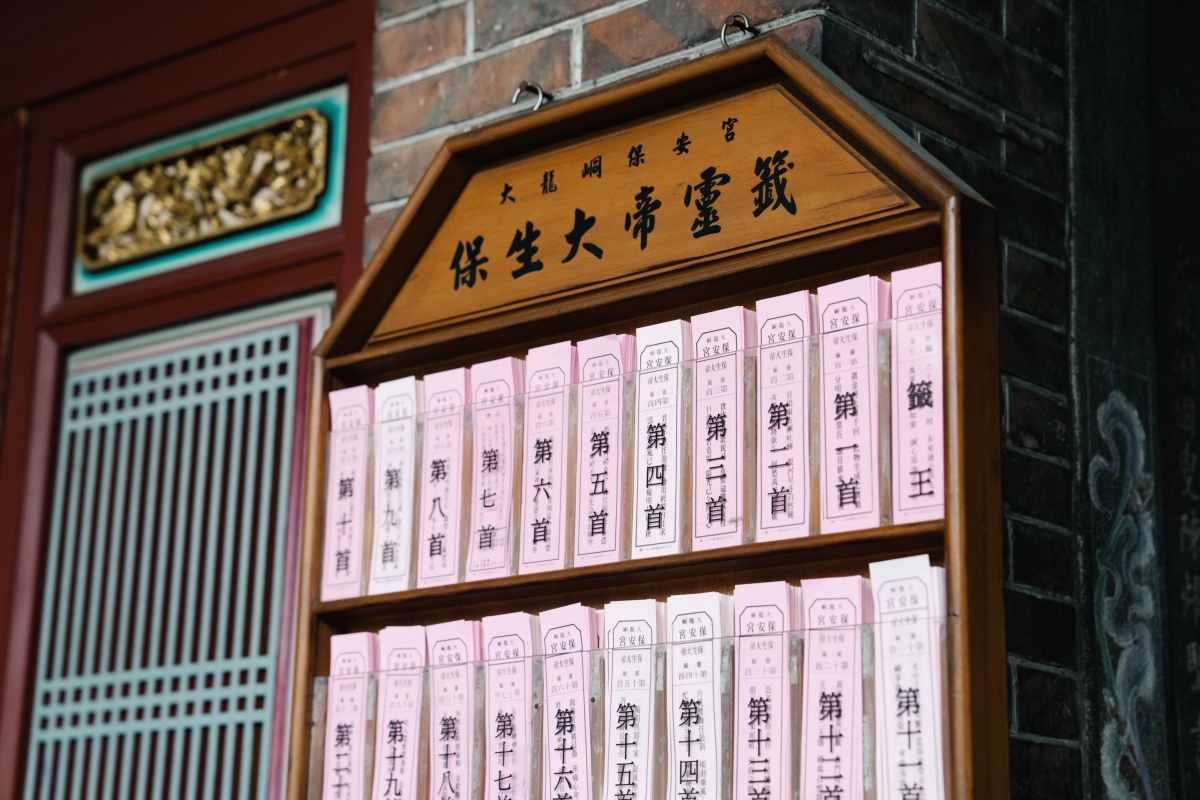當曾經帶著台灣衝上經濟高峰的代工產業逐漸沒落,難道就只能向當時身經百戰的工藝技術含淚說掰掰?從神秘的「跳台」工藝為起點,我們直奔豐原,專程拜訪台灣碩果僅存的跳台師傅阿煙,一起重新發現那段台灣木產業的黃金時代!
我們前往豐原拜訪「跳台」師傅阿煙(江隆煙)的那天,滿載的車廂裡幾乎都是商務客的身影,魚貫走出車站人潮各自散去,南來北往都有,倒是和我們同方向前往豐原的車流並不多。其實,早在民國五○年代,豐原可說是台灣最鼎盛、商辦川流不斷的木業重鎮。根據豐原漆藝館的官方資料,當時僅僅是木業中的漆器產業,極盛時期的年外銷金額就高達五、六億元,直接或間接從事漆器生產的工廠達30~40家,就業人口也有2~3千人,由此不難想見整體木業在豐原的盛況。然而,隨著產業環境變化,現在豐原的木業景況已經今非昔比。仍持續運作的木工廠已經不多,而像是阿煙這樣仍持續使用昔日「跳台」技術的師傅,幾乎已經找不到。
旋轉、削鑿、跳一下 豐原黃金時代的跳台工藝
民國七○年代,當時20多歲的阿煙碰上了豐原木業的黃金年代,「那時候外銷量很大,一筆訂單下來,就專做同一件產品,可以做一整年都不用換模具」。豐原的木加工業興盛,其實與國際間的代工出口有很大的關係,民國58年(1969年),日本國內禁止開採天然木、加上工資上漲,由美國出資、日本提供設備和技術的「米爾帕赫羅工廠」(當地人都習慣叫它「美國工廠」)於是選擇來台設廠,阿煙師傅年輕時最擅長做的「沙拉碗」,就是美國工廠的主力產品。
而在那個CNC(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技術才剛發明、尚未普及的年代,每一件擁有圓嘟嘟弧線造型的沙拉碗,都是師傅們使用「跳台」手工製作出來。初聽到這名稱,有養貓的人大多會想到「貓跳台」,但其實跳台跟貓一點關係也沒有,而是從以「旋轉」和「削鑿」為原理的「車床」改良而來。
跳台這獨特的技術來自於日本福島縣的會津地區,將原本的車床加上模具,不僅改良了徒手操作時成品水準良莠不齊的問題,還能隨著師傅在機台前後的「跳躍」換位,一次完成器皿內外的形狀。而這獨特的跳躍動作,也就成為「跳台」名稱的由來。
「市場好的時候,光是跳台,豐原一帶就有2,000多台。銷歐美的沙拉碗、或是日本人送禮會用的漆器糖果盒,只要有做就賣得出去」,那時期豐原所有的年輕人幾乎都在木加工產業,和阿煙同輩的家族兄弟和朋友們,做跳台、做烤漆的都有,「但是,大概民國80年之後,台灣禁伐天然林,加上中國開放和更低的工資,我做不到十年環境就變了。」
代工的休止符,或是轉型的起手勢?
就像是阿煙親身觀察到的變化,在全球化競爭的時代,擁有代工需求的大廠就像是獵鷹般,以銳利的視角掃視各國,有低廉人工、豐富資源的地方,就是水草豐美的遷徙目標。三十年前的台灣、二十年前的中國、到近十年的東南亞⋯,代工重鎮的流動移轉是產業的必然。
雖然豐原的木加工業早已不復當年盛況,但阿煙還是選擇繼續做下來,問起原因,他爽朗地笑說「啊都做這麼久了」。長時間練就的好手藝,讓阿煙在大型代工產業外移後,還曾在民國八〇、九〇年代,分別受邀到越南和中國教導當地人如何以跳台製作沙拉碗。而在台灣,當時一年到頭做同款都不用換模具的量產大單,變成一個模子只做幾十、幾百個的小訂單,和阿煙合作的對象,也從美國大工廠,變成台灣在地的小型設計品牌。
代工盛況的來與去,不僅標示著台灣經濟轉型的歷程,以技術的角度來看,代表著這樣的工藝已經通過市場的考驗,既具備純熟的技法、也能達到一定的量產數。也就是說,台灣木產業的現狀,從一個層面看來,是代工極盛而衰的事實,但換個角度想,像阿煙這樣擁有一身好手藝,又能理解量產重要性的師傅,對於近幾年興起的台灣獨立設計品牌來說,的確有機會能相互支持闢出一條產業持續轉型的新路徑。
編輯、出版社熱血撩落去 跳台杯站上嘖嘖拚募資
儘管這新路徑讓人充滿期待,但一切倒也不都是那樣水到渠成,許多重要的前提還是有的,比如說合作雙方的「觀念轉換」和「工作習慣磨合」。而這樣的過程,也呈現在這次行人文化實驗室(後簡稱「行人」)隨著《成材的木,成器的人》延伸出來的「阿煙的木製杯」在嘖嘖上的募資計畫。
由阿煙以跳台全程手工製作,加上設計師高立杰設計出的小酌杯、日常杯、喝茶杯三種杯款,是「阿煙的木製杯」計畫的主力商品。雖然這次過程中,設計師和阿煙師傅只見過一次面,其間都是由行人團隊來回奔波溝通,但即使是隔空聯手,對於原本就從事木材質產品設計、且時常與工廠及師傅合作的高立杰來說,經驗累積出的合作眉角絕對重要。
「阿煙師傅那邊不太像是工廠,或許是因為規模小,比較像是現在日本的工坊。那些日本知名工坊的作品出現在各國知名選物店,其實,他們很多就只是幾位師傅日復一日,以純手工一件一件的製作著。」回到合作眉角的話題,高立杰進一步解釋,「無論是工廠或是工坊,設計師和他們合作時,都要從工廠的角度來想事情!要讓對方知道我懂你的困難、也知道技術面的方法,不要讓人家覺得,你們設計師就是只會畫圖。試著換位思考,彼此有了這個相互理解的共識。接下來,要一起克服挑戰才有可能。」
那一只阿煙覺得很丟臉的破杯子
除了設計師的思考模式轉換,對經歷過代工外銷盛況的師傅來說,或許在他們心目中,產量先行的概念仍是做產品時的最習慣切入角度。然而,當大環境對量的需求不再那麼迫切,什麼是新的著眼點?
「嗯,我們做這件事情的初衷,的確不全然是為了市場」,帶頭催生這一系列計畫的總編輯周易正回答得直率,「我記得聽過小米的創辦人雷軍說,他不確定自己的產品是不是成功,但他確定小米改變了大陸的生產鏈對品質的要求,我不知道這樣比喻會不會有點誇張。但回到這次企畫,一方面就是要讓師傅覺得做這件事,是有價值、有意義的。師傅不是又完成了一件產品,而是希望藉由合作過程,引出他內心匠人態度的那一面。」
在《跳台與木器:未完成、完成與待續》的展覽大桌上,一只杯壁過薄而斷裂的杯子就放在正中央展示,「我們跟師傅要那個破杯子的時候,他一直說為什麼要拿那個,很丟臉耶」,行人團隊的企劃經理華郁芳笑著回想起這段對話,「對我們來說,破掉的杯子其實很感人,那就是阿煙師傅對杯壁薄度極限的自我挑戰。」
點燃匠人魂的小火花
和以往量產沙拉碗時不需處理的薄度交手後,阿煙師傅挑戰的還有木器折角的銳利度,無論是跳台或車床,原本的強項就是做出圓弧,但若想要適時地強調木工藝技術,以「喝茶杯」來說,側邊杯身是否成直線、杯底折角是否夠銳利,就是看點所在。據說,雖然行人團隊反覆提醒,剛開始阿煙師傅做出的杯緣仍不免帶著弧度,但經過了這幾個月的來回,到我們造訪的那天,阿煙師傅很自然地拿出一把直尺緊靠在杯身上,瞇著眼邊測邊說,「現在應該有直了,這樣檢查一下比較準。」
我們好奇問起阿煙師傅,做過最有挑戰性的木器是什麼?「最難的喔,就是這次他們的那三個杯子啊!」阿煙看了一眼行人團隊們,「像是杯口故意做窄、很難邊做邊看到杯子裡面狀況的那個大杯(日常杯);另一個(小酌杯)杯底又故意縮很小、模具很難卡穩,都很難做喔。」儘管隨口說說難處就是一串,但當眼前那通過高標檢視的成品抬頭挺胸地站成一列,阿煙師傅言談間低調又微微帶著自豪感的聲線,看來那股潛藏在阿煙心中的匠人魂小火苗,已經燃出火花!
行人文化實驗室
通常是一間出版社,但更常在做一些實驗,例如,假裝自己也是作者。用打群架的方式,找到一個目標對象(議題/主題),再找來一群堅強的夥伴(採訪/攝影/設計......),不被時間牽著鼻子走(所以不是定期出刊),只在乎打一場有把握的勝戰。為議題/主題找到新的觀點、思考方式、甚至是讓它延續與存在的可能。過去作品有《活字:記憶鉛與火的時代》、《咆哮誌:突破時代的雜誌》、《討海魂:13種即將消失的捕魚技法,找尋人海共存之道》、《臺灣妖怪研究室報告》、《透明的記憶:感受日常玻璃的溫度》、《成材的木,成器的人》。
文/方敘潔
攝影/張藝霖、方敘潔
圖片提供/行人文化實驗室
【完整內容請見《LaVie》2017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