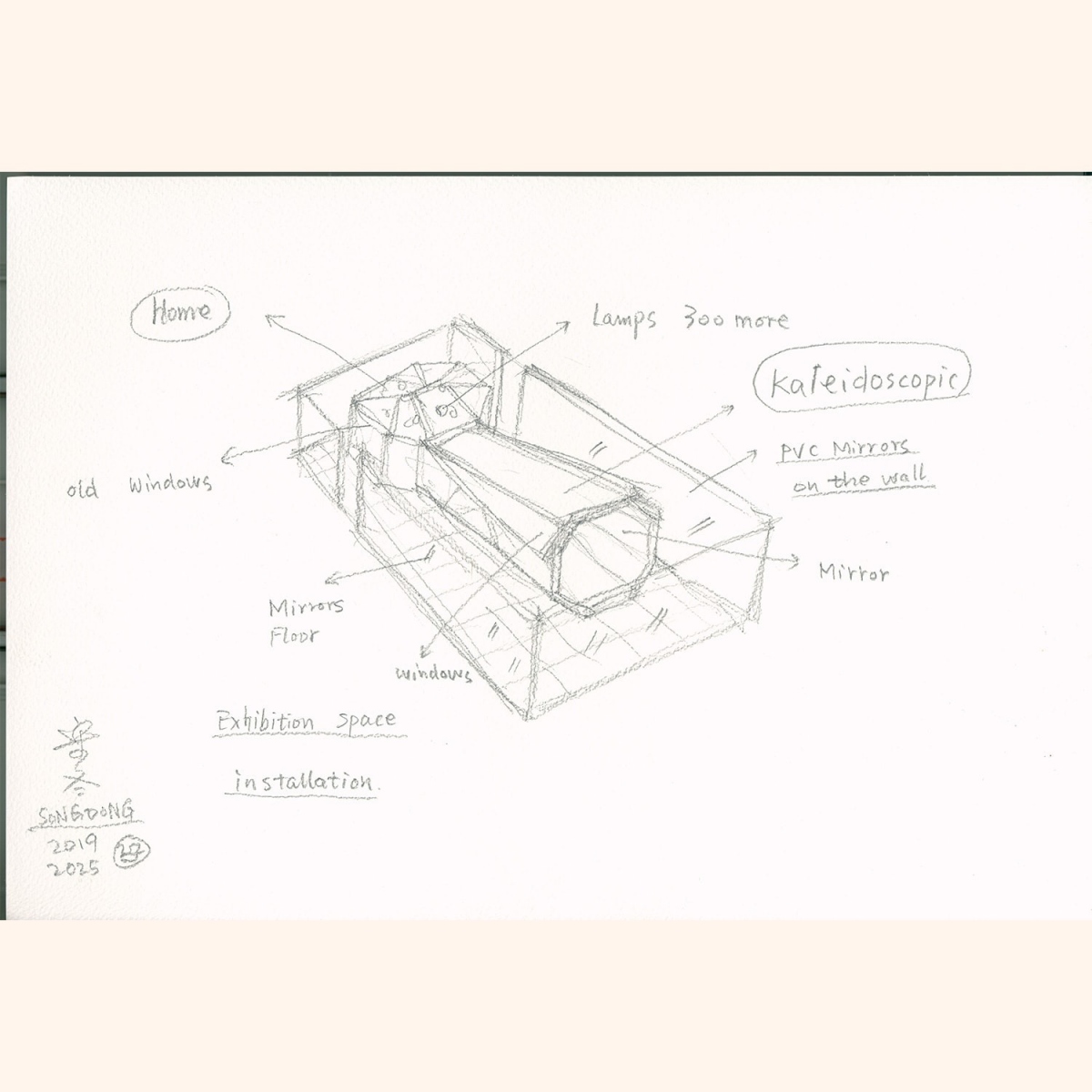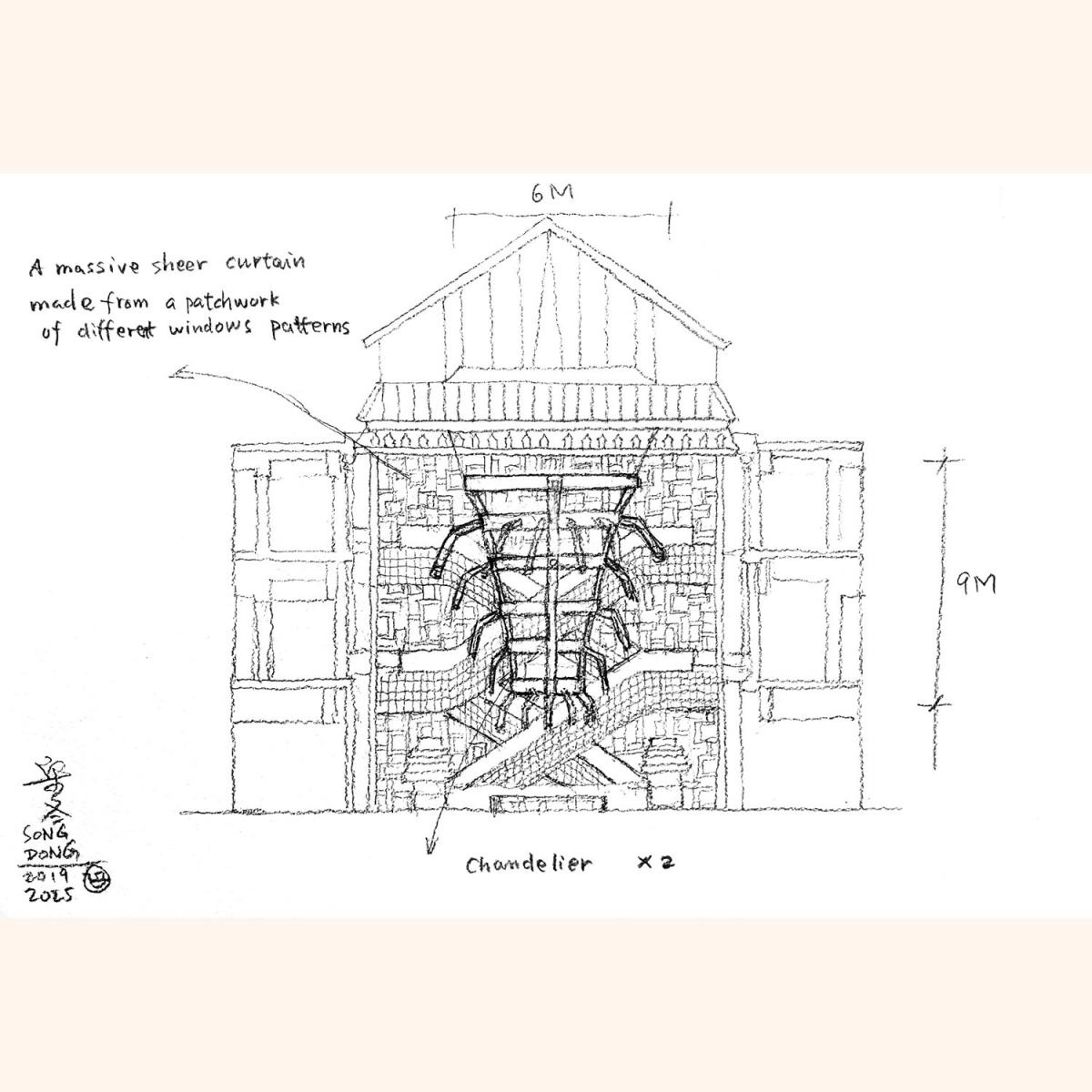2018年第11屆台北雙年展正式登場!作為台灣當代藝術界的年度盛事,2018台北雙年展將在未來四個月於臺北市立美術館(北美館)亮相,本屆展覽集結來自世界各地19個國家及地區共42名藝術家與團隊,一同引領大家進入「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
本屆台北雙年展由吳瑪悧與來自義大利的范切斯科馬納克達(Francesco Manacorda)共同策展,主題定調為「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這點或許能正於北美館戶外大廳所展出的《預許之地》裝置藝術(非本屆雙年展作品)便能嗅出一些端倪。兩位策展人希冀將北美館這幢白盒子,化身為探究人與自然之間,交互且緊密相聯的生態系統結構,讓展覽地點變身為社會實驗平台,藉以建立持久、社群取向,由下而上的協同作用,打開跨學科的討論與全新可能。
為實現此策展核心觀點,兩位策展人邀集了多元的參展名單,包含視覺藝術家以及非營利組織(NGO)、社會運動人士(activist)、影像工作者、建築師等,以此打造跨界對話的論述場域。對於本屆雙年展參展名單,策展人吳瑪悧特別表示,兩位策展人採取「創意實踐者」特質定義每位參展者與團隊,從而挑選出最終的參展計畫。而參展者亦非僅限於展覽現場靜態展出的計畫創作者,兩位策展人認為連同雙年展論壇的講者和與談人、參與響應展覽中「生態實驗室」的公民團體,都是參與展覽的創作角色、議題的實踐者。
在「後自然」的命題與「生態系統」的觀點下,作品觸及議題包含人類與環境生態的關係如外來物種對當地生態的衝擊、自然環境議題如土地及空氣汙染、氣候及環境變遷議題如地景及氣候改變等。不同議題在展場中並陳、展開對話,藉以讓美術館的展覽空間在議題討論的面向發揮積極功能,具體回應「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的策展命題!
馬納克達表示:「今年台北雙年展架構與方法論的核心要點為鼓勵來自不同領域參與者的相互交流,以及對於對話語彙的探索。重新協商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兩者相互依存並交互影響的關係成為本次國際論壇的主幹。我們希望觀眾可以通過此次雙年展得到啟發,在未來尋找一個更可持續發展的嶄新看法與解決方案。」。
2018台北雙年展藝術作品亮點
一樓展區
亮相北美館大廳,由藝術家亨利克赫肯森(Henrik Håkansson)所持續發展的《顛倒的樹(映射)》藝術作品率先揭開本屆雙年展序幕。一株在地樹木被倒掛、於地板上方停懸,被物化的樹成為一件雕塑;藝術家在此挪用了杜象將非藝術轉移到藝術空間的概念。樹枝在樹冠上方和下方的鏡子中無盡反射,這株單一的樹喻指所有樹種,以及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與對它的剝削。
關於作品,赫肯森表示《顛倒的樹(映射)》一方面實驗性地用一種轉化方式表現自然,另一方面也強化了體現任一樹木所處的環境。這種環境卻處在一種脆弱的狀態,在雙鏡子創造的無限空間中,諸如生與死、具體與抽象、組織與混亂等對立狀態,反而呈現一種相互連貫而非永不相容的特質。
阿根廷藝術家薇薇安蘇特(Vivian Suter)長期居住於瓜地馬拉西南部的高地。藝術家平時進行創作的空間並不侷限於室內或戶外,常是在作品完成後再藉風雨、昆蟲、泥土、植物等自然元素的力量輔助完成。蘇特對大自然的描繪,並非採繪畫式風景或闡述性的畫像,而是以豐沛的直觀情緒表現身邊環境給她的感受,因此深受四季更迭與各類劇變的影響。蘇特在台北雙年展展出的全新繪畫系列,是她造訪台灣在拉拉山的茶園,以數天時間進行的創作,讓自己從瓜地馬拉的工作室環境抽離,把對臺灣風土人文的第一印象引入到作品裡。
走進一樓會展後,許多壓克力的圓形球體赫然出現在眼前,這是由多組海內外藝術家所組成的菌絲網絡社會(MNS)集體計畫。菌絲體是真菌細胞線狀網絡的總稱,負責分享和處理訊息,菌絲網絡社會為台北雙年展製作了一個大型菌絲網絡模型,展示其傳遞訊息的能力和與其他植物共生的行為。
該裝置以真菌產生的棒麴黴素(Patulin)分子結構為原型,由17個長有靈芝菌絲體的透明壓克力原子和特製的感應器、發射器、接收器所組成。這些電子設備偵測到活體菌絲原子內的物質變化後,透過無線電頻率傳輸訊息;訊息被空間化並轉化為可在裝置中體驗的聲音。菌絲網絡社會是一個於 Stadtwerkstatt(奧地利林茲)與cycleX(紐約州安地斯)發起的行動。該網絡目前在法、英、美三國共有六個節點,最近在台灣新增四個節點。
藝術家烏蘇拉畢曼(Ursula Biemann)新作《聲海》揉合科學、個人、現象學的敘事觀點,探索海洋的深度和挪威北部羅浮敦群島水線上下的種間關係。最新科技研究在這部科幻詩風格的影片中與古老的知識及海底的聲音相互攙和。
台灣藝術家張碩尹《溪山清遠》 則在展區打造一區看來頗有人文雅趣的書畫空間,然而所陳述的卻是越來越嚴重的空汙問題。作品製作過程包括蒐集台北市不同地點的空汙,再將空氣中的懸浮微粒製成墨汁,同時以影像紀錄呈現蒐集過程。作者也邀請氣喘患者參與六週的工作坊,在藝術治療師帶領下,以此墨汁進行繪畫性表達。作品呈現空汙對社會、家庭與個人所產生的影響,同時希望透過病患共同製作的繪畫,作為一項社會提案。
沒有人是局外人!「原轉小教室」是由紀錄片導演馬躍.比吼、音樂人巴奈、那布等原住民藝文工作者,以及關心土地的各族群朋友共同組成。此次展中《凱道運動場》,將延續凱道駐紮與集體創作的「運動」精神,彰顯訴求台灣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帳篷倒置懸掛在空中,布滿標語的「運動毛巾」無聲地喧嘩,混沌洪荒的石頭環圈,帶有某種古老儀式的原型意味。環形中形似百合花的裝置作品由各方募集的原住民運動物件編織而成,那是凱道部落數百天來從冰冷的都市水泥中綻開的花朵。
文件展的形式則以巨型的圓錐竹架,將近代臺灣原民運動乃至凱道大事紀、以及凱道紮營累進天數等「時間」架構貫穿其中。透過七場「凱道小講堂」與行動紀錄的影像文件,期將原住民傳統領域議題引入美術館中,激發討論與互動,形成一個有機的生態空間。
尼古拉斯曼甘(Nicholas Mangn)的作品《白蟻經濟學》,由嶄新敘事的錄像檔案及雕塑作品所組成的裝置藝術中,尼古拉斯曼甘調查了由該段軼事所構成的問題:白蟻如何作為礦工及世界建設者,在更易被理解的人類社會及經濟結構中被雇用?
德國藝術家英果古騰(Ingo Günther)則帶來本次展覽最奇幻的《世界處理器》裝置作品,這個從1988年迄今發展的項目,以「世界處理器」為名多方試探如何在球體上映射地球的數據,例如國家健康統計資料、生育率、國防預算、毒品販運路線、遷移模式、貿易趨勢、海底光纖網路、媒體自由等。
《世界處理器》至今已做出1000多個地球儀,力求改善我們在知識面與情感面的遊歷世界經驗。為了將政治、經濟、社會模式繪製在地球儀上,藝術家需重新配置地球儀的表面,以顏色區分民族國家,他將發明至今已五百多年的地球儀更新,以反映當代全球化狀態。
二樓展區
台灣藝術家蕭聖健的《歸》,則在展區中打造出一個工業鳥鳴大樹。展場中央置放轉盤,透過緩慢旋轉的樹幹切片,控制鳥鳴器叫聲的位置變換,並且模擬鳥群從一棵樹集體移動到另一棵樹的聲效。在燈光和交錯的電線裝置裡,製造出一種黃昏樹影的意象。
《大佛普拉斯》導演黃信堯,此次在2018台北雙年展也拍攝紀錄片《印樣白冷圳》關注水圳本身,亦詮釋水、山林土地與人的連結。如果生命有源頭,那川水的源頭就來自於山林,河道就像是水的生命旅程。而白冷圳有如生命裡的一段插曲,雖然細微,卻影響著往後的旅程。
馬來西亞藝術家區秀詒此次帶來三頻道錄像及聲音裝置《椰林、檳城艷與情報員的生死戀情:一次放送計畫》,以臺灣殖民地作背景,消失的情報員和檳城艷的「生死戀情」為敘事核心,模仿1935年臺灣博覽會南方館以仿真橡膠林展示當時馬來西亞的面貌。而二十世紀初期,日本帝國以實驗室名義,將臺灣建造成南方之最北端的樂園,作為征戰南洋的預備地。作品讓觀者在一個精簡視覺與聽覺語彙的空間裡,重新想像日本——臺灣——馬來西亞間,以行進的自然為名,所交織出的複調關係。
張懷文與MAS微建築研究室,除了在本屆台北雙年展精選了過去針對分布於全球各種氣候與地域條件所提出的30件建築概念設計作品外,也帶來全新《北美雲》裝置藝術,作品位於北美館入口區西側二樓的管狀空間立面,由館外與館內皆可見,並與設置於美術館屋頂的氣象站互動,將美術館的微氣候視覺化,是一件為期兩年呈現、記錄北美館微氣候的創作計畫。
地下展區
藝術家林從欣的《字花》(2018年)關注植物如何與人類生活相互糾纏,《字花》種植罌粟科植物、甘蔗以及加勒比海地區有毒植物在由紅土和鳥糞組成的土床,裝置作品的中心是壓印在土中的人形,代表「字花」中的人物輪廓。展覽期間作品會被每天予以照顧和澆水,讓植物生長。作品追溯鴉片罌粟成癮如何被武器化,以及如何被歐洲人用來作為生物政治手段以操縱貿易優勢,藉以指涉深藏於社會結構中的奴役與移民、人口販運等議題。
藝術家圖爾格林富特(Tue Greenfort)注意到北美館三層樓高的玻璃中庭,尤其是從冷氣房進入這個空間時身體的感受。中庭裡面除了有植物,還為美術館員工提供陽光和空間,讓他們可以在自然般的環境中吃東西、休息、聊天、做運動。
在這中庭裡放置有數件大型混凝土盆栽,他發現盆栽扮演著重要角色,它們已經成為白頭翁的家——台灣的地方性鳥類,經常被作為鳴禽圈養。他在美術館拍攝的《白頭翁》則捕捉它們照顧巢穴和幼鳥的畫面,也拍到白頭翁進駐中庭後對人類社交活動產生的催化作用,八分多鐘的錄像裡可以聽到白頭翁的叫聲與建築物上方掠過的飛機聲交疊,中庭呈現了人類、動物、科技之間三角關係的縮影。而中庭豎起的三根黑色柱子,則依循古老真菌化石的樣態,在上面培養蠔菇。
2018台北雙年展
時間:2018.11.17 – 2019.03.10
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
文字編輯:Ian Liu
via 北美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