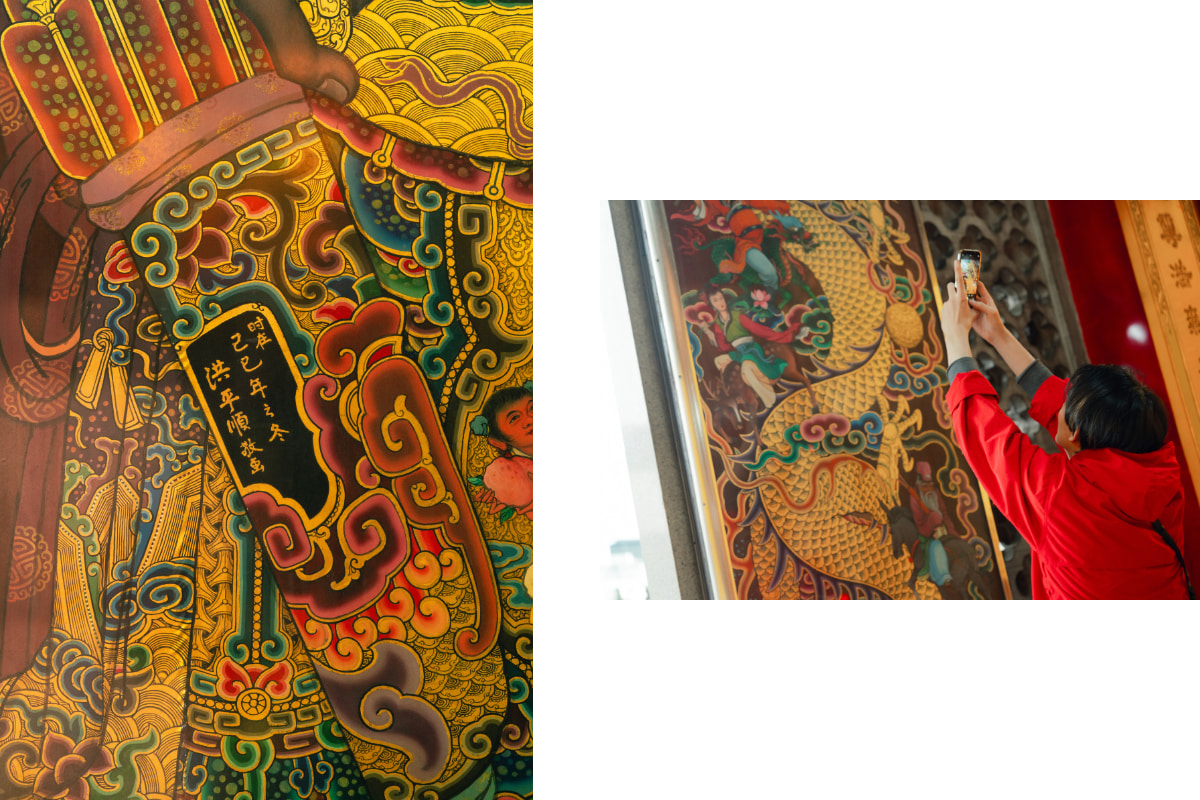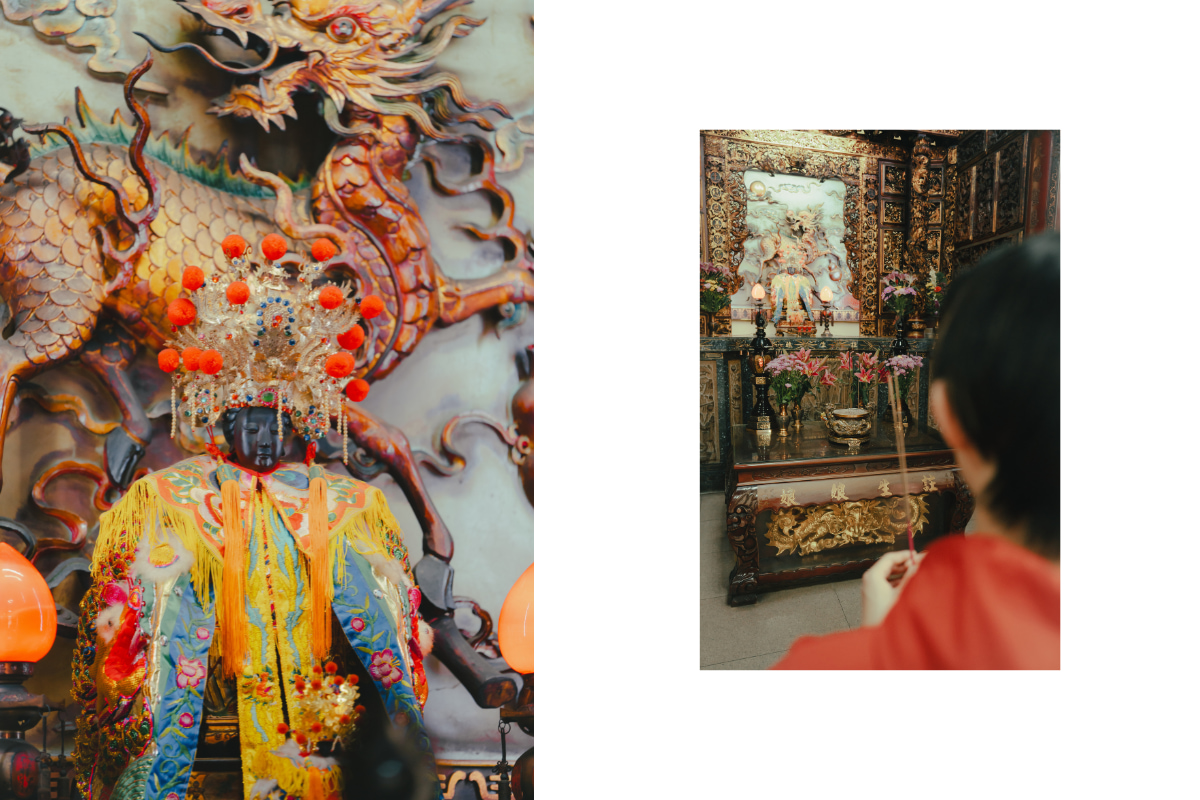北美館「塩田千春:顫動的靈魂」於2021年5月1日開展,是藝術家塩田千春最大規模回顧展,她接受La Vie專訪時,和善而謹慎,娓娓道出對創作、對記憶、對認同等的看法。讓大家走進北美館看展之餘,有機會能更深入了解藝術家的創作本質。
補充說明,2021年5月受疫情影響而閉展,已於7月13日以「預約」方式,重新對外開放。
>>塩田千春來台佈展的策展巧思!必須與空間互動、無法被複製的作品
走進現場思考各種可能
La Vie:2019年森美術館辦了大型回顧展《塩田千春展:靈魂的震蕩》,66萬人次進場,成為森美術館史上來館人數第二高的展覽。您創造的巨大裝置,有什麼設計,能把觀眾捲入那個世界裡,和觀者的記憶共振呢?
塩田千春:沒有什麼技巧,只是全心全意投入創作,我只想著這件事。個展時我會花很多時間,一有空就到現場,在裡面反覆地走動,想像絲線的樣子,要怎麼編織,怎麼安放。


La Vie:有人說您的作品是沉浸式劇場,您覺得呢?
塩田千春:可能有共通之處。生病那兩年,直到癌症療程結束,我都還是在想巡迴展要創作什麼樣的新作。後來從醫生手上拿到抗腫瘤藥的空盒,我在裡面放了會發亮的聖誕燈飾,擺在病床邊,也加進發光的點滴,做了作品。跟策展人片岡真實說,她回我「不行,太強烈了。做到這個地步的話,誰都無法進入作品。」不過當時,我還不知道到底哪裡不行。是跟自己太接近了,但那時候不做那件作品的話,我自己也活不下去。因為我就處在那種情境裡。
現在想起來,那種作品無法讓人同感,無法讓人進入。創作的好處是,自己能擁有跟本來不同的他者之眼,能隔開距離。絲線創作也是,碰觸絲線的時候,感覺自己變成了他人,距離產生後,能夠置身客觀立場。所以,觀者也比較容易進入作品世界吧。我其實展出過那個作品,但是自己看都覺得難受,像宣洩式的嘔吐,如同片岡說的,「還算不上是作品」。

臺灣印象:開放、親切又美味,但不利拍照
La Vie:您來過臺灣嗎?對臺灣的印象如何?
塩田千春:第一次來臺灣。我提到過入境審查表格的事,性別欄設了男性、女性及其他,我很感動。在全世界旅行,我第一次看到這種設計,真是好開放的國家。
隔離期間一步也不能踏出房門,不時會有關心簡訊,問我今天怎麼樣啊之類,很親切。每天提供三餐,有時我想不吃晚餐,「可是晚上是傳統臺灣料理喔」,被這麼一說,只好回「那我還是吃好了」。「今天中午不用」「中午是松露燉飯」「那就麻煩了」,其實內心之聲是不要再誘惑我了。(笑)
這樣每天固定吃三餐,越來越胖,出關後面對媒體採訪,相機咔嚓咔擦,卻是我最胖的時候。實在是……隔離閉關式的環境對創作者來說很好。出關後只在展間做裝置,很少去外面。
物靈與纏繞的記憶
La Vie:您實際收集現場的物品,用藝術手法再現時間和人們的生活。收集物品的工作,讓人想起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博物館。凝視這些纏繞於物上的記憶,和集中營黑暗記憶的再現是否相通呢?
塩田千春:去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時候,比克瑙原封不動保留了當時的東西,在寒冷的冬日,眼前感覺就是殺人工廠,實在無法相信,記得看的時候寒毛直豎。不過,博物館展示很樸素,和我的作品不一樣。但那些「人們曾經擁有的物」的概念,大概沒什麼差別。我自己沒有以奧斯維辛集中營為主題創作過。
我使用人們穿過的洋裝、鞋子和皮箱等物品創作,可能因為這樣,和奧斯維辛有相近之處,集中營意象很強。我在離奧斯維辛最近的城鎮克拉克夫展示關於鞋子的裝置作品時,也有人提到了跟奧斯維辛的關係。但是在大阪展示同一件作品時,完全沒人說到奧斯維辛,他們用「舊鞋藝術」來看那件作品。在不同國度,人們思考作品的角度完全不同。

存在從不存在中透顯出來
La Vie:從病床或船艙中展開的無數的絲線,讓觀者感到記憶的幽黯,甚至毛骨悚然。您提出的命題:不存在之中的存在,讓魂或是靈等本來看不到的東西具體化為可以看到的形狀,您如何探尋出具體化的手法?
塩田千春:我會收集別人用過的物品,人用過的東西和新的東西不一樣。像是我在大阪展收集鞋子的時候,不要新鞋,一定要別人穿過的鞋子,而且最好附上使用者的話語,我希望對方寫下跟這件物品的故事:那是他因為想開麵包店,拚命工作時穿的鞋子;結婚時或小孩運動會時穿的鞋子,或是丈夫去世時穿的鞋子……也有坐輪椅的人的鞋子,但沒機會穿著走路,寄來的時候鞋還是全新的。
看著這些東西,好像看到回憶的照片。我用絲線再串連起物品裡的記憶,如此一來,從不存在裡,存在漸漸透顯了出來。
絲線與空間的對話
La Vie:在編織「絲線」以前,是否會描繪素描或設計圖?
塩田千春:我感覺是用絲線直接在空間裡繪圖,是視覺化的,在畫面這邊畫了線條以後,接下來在那裡畫一筆,我想抓住一種直覺,那中間的「緊張感」很重要。我不畫設計圖,我和空間對話。

和老師們的時光
La Vie:告別油畫媒材,尋找自己的創作方式時,您與行為藝術家阿布拉莫維奇和瑞貝卡.霍恩等大師相遇,受到了什麼樣的啟發?她們是怎麼上課的?
塩田千春:在阿布拉莫維奇的工作坊時,進行了一週的斷食課程。當時在法國鄉間,大概有15個學生左右。她會叫我們在幾個小時以內,不斷寫自己的名字。會要學生相對坐著一個小時以上,一動也不動地看著彼此。有天繞著湖走,第二天要我們戴上眼罩再繞湖一次。
(La Vie:感覺是把身心逼到極限?)
對!在那種情境下,會感覺到自己的內在,忍不住哭叫出來。反覆做那些日常生活中幾乎不會做的事,會看到不同的觀點,隨之產生不同的自覺。
說到雷貝卡,她很害怕鳥,但是她的作品,製作了很多裝上鳥翅膀和被鳥羽毛環繞的裝置。因為恐懼,於是觸碰恐懼,這種創作,讓我感覺到人類很有趣的部分。
(La Vie:直接面對恐懼的態度,和您的創作方式也有關係?)
塩田千春:嗯,可以這麼說。

我○○人的身份逐漸清晰/模糊
La Vie:關於《集聚-尋求目的地》,您寫道:「由於生活周遭充滿了各國人士,常常一時之間忘記自己來自日本。及至看見鏡子裡的倒影,才猛然發現我是黑頭髮黑眼珠的亞洲人。」從〈皮膚的記憶〉、浴室行為藝術到現在,您持續探索自我認同,在德國和日本各待了人生的一半時間,現在怎麼看認同問題?
塩田千春:「我到底是什麼?」我是從這個問題開始,像尋找答案般開始創作。但在國外越久,混在不同的人群中間,我好像越能看到自己。
這次來臺灣,明明是外國,但待在亞洲人的環境,反而有種新鮮的不習慣。我很驚訝這裡是外國,感覺到完全不同的「異國感」。
La Vie:新冠病毒的蔓延,有改變目前在歐洲亞洲人的處境嗎?
塩田千春:一開始病毒是從中國來的,所以亞洲人被歧視,但現在歐洲的狀況更嚴重,德國一天兩萬人確診。比較起來,臺灣是世界上最好的吧,臺灣和紐西蘭,
(La Vie:希望您在安全的臺灣再待一陣子吧!)
塩田千春:真的,我很想!

>>北美館館長王俊傑新上任!計畫籌備二館、人才培育、國際共製 不做簡單的事
塩田千春:顫動的靈魂
展期:2021.07.13起,線上預約進場(週一休館)展覽至10月17日
地點:北美館 一樓 1A、1B 展覽室
票價:全票30元/優待票15元
採訪整理|高彩雯
圖片提供|臺北市立美術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