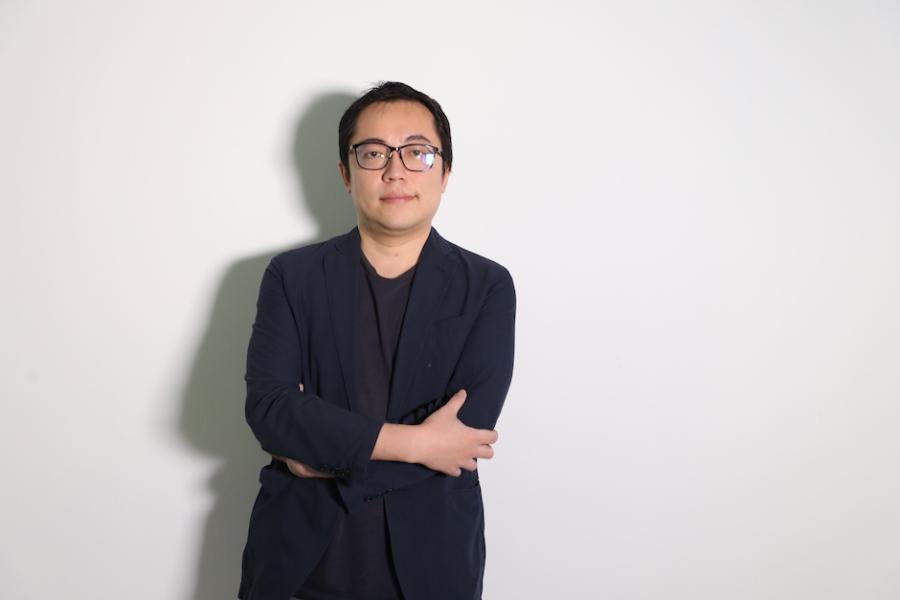袁廣鳴、李亦凡,師生兩位分屬不同世代的錄像與新媒體藝術家,分別代表2024與2026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台灣館。袁廣鳴《日常戰爭》凝望生活裡的失序與脆弱;李亦凡《鬱卒的平面》則延續他特有的黑色幽默,翻玩數位虛擬世界的邊界。此次相談,他們從科技與藝術的拉鋸戰中,試著探看未來創作的可能。
拾級而上,清幽山腰間袁廣鳴的家樓頂便是工作室,2024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台灣館作品〈日常戰爭〉的1比1模型場景才正準備要拆除,以容納他的下一部創作。李亦凡學生時期也曾在這裡幫忙施作部分場景。
談到李亦凡的作品,袁廣鳴著迷於其中帶點邪惡、挑釁的幽默感。他舉例其第1個動畫作品《海邊散步》(2011),大笑說:「很驚豔、很妙,怎麼會這麼下流!」他形容李亦凡的創作「會讓人想笑,背後又有某種批判性或思考。我太嚴肅了,我的作品可能也有種黑色幽默,但很難讓人笑出來。」他也觀察到,李亦凡很早就結合操偶(puppet)與3D影像,這方向在台灣錄像藝術領域較少發掘,對他來說非常有趣。
倒是李亦凡回憶起近身觀察的時光,「我們都是需要邊做、邊看,很難事前緊密規劃。記得每次到一個段落,老師常說:『覺得哪裡怪怪的?』對我來說,這種工作模式是創作上珍貴的啟發—要在做的過程中親自去感受,才去判斷對與不對並做出調整。」其中不乏有機的意外,卻也造就創造的可能性。
李亦凡
藝術家,1989年生於台北,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研究所,現於荷蘭Rijksakademie駐村。創作結合遊戲引擎、即時影像與自製工具,常以黑色幽默與獨白式敘事探問人在數位環境中的感知、慾望與焦慮。曾獲台新藝術獎、銅鐘藝術賞與高雄獎,展覽遍及歐洲與亞洲。2026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代表藝術家,將以《鬱卒的平面》回應影像與科技的時代處境。
袁廣鳴
台灣錄像藝術先鋒,1965年生於台北。1997年取得卡斯魯造形藝術學院媒體藝術碩士。自1990年代起,他以單頻錄像、動力裝置、空拍影像與高格率拍攝,持續揭露日常背後的不安。〈棲居如詩〉(2014)以爆炸倒帶結構直指安居幻象;〈佔領第561小時〉(2014)記錄太陽花學運的集體場景;〈日常演習〉(2018)以5台空拍機凝望萬安演習。2024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代表藝術家,展出《日常戰爭》回應全球化與科技中的失序與脆弱。
Q:兩位的創作最初都是由繪畫出發,你們為何轉向錄像或說新媒體藝術?
袁廣鳴
李亦凡
袁廣鳴
VIDEO
Q:身為不同世代的錄像創作者,自認差別可能在哪?
李亦凡
袁廣鳴
李亦凡
Q:你們算是某種程度上的「技術宅」嗎?工具與技術會如何決定創作上的創新?
李亦凡
袁廣鳴
李亦凡
袁廣鳴
VIDEO
Q:近期你們準備挑戰什麼樣的創作?
袁廣鳴
在YouTube上,我發現有一類心靈療癒、「顯化」的影片會播放冥想音樂,標題像是「I’m good」、「I’m gorgeous」還有「I’m rich」等等,點閱率超高。我一開始不明白誰在看,但後來反思到,許多人非常努力但人生運氣不好,這種心理創傷具有一種普世性,我想藉由這種影片形式探向人性脆弱的部分,在其中藏些矛盾讓觀眾神經錯亂。
VIDEO
李亦凡
網路社群上所謂「P圖公社」有種新的發文趨勢:請你幫我把過世的親人P出來, 甚至讓他動起來講話。這很可怕,那感動到底是什麼?該不該感動?但又不能否認那個情緒的存在。此外,使用這些雲端工具與服務大都必須透過大公司才能運作, 那同意條款中其實藏有很多有趣的條目與禁忌。
Q:一路走來,你們覺得人們對「創新」這件事有什麼想法?
袁廣鳴
李亦凡
採訪整理|吳哲夫 攝影|羅柏麟 攝影助理|黃品瑜 圖片提供|各單位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La Vie 2025/12 月號《秩序重啟Order Res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