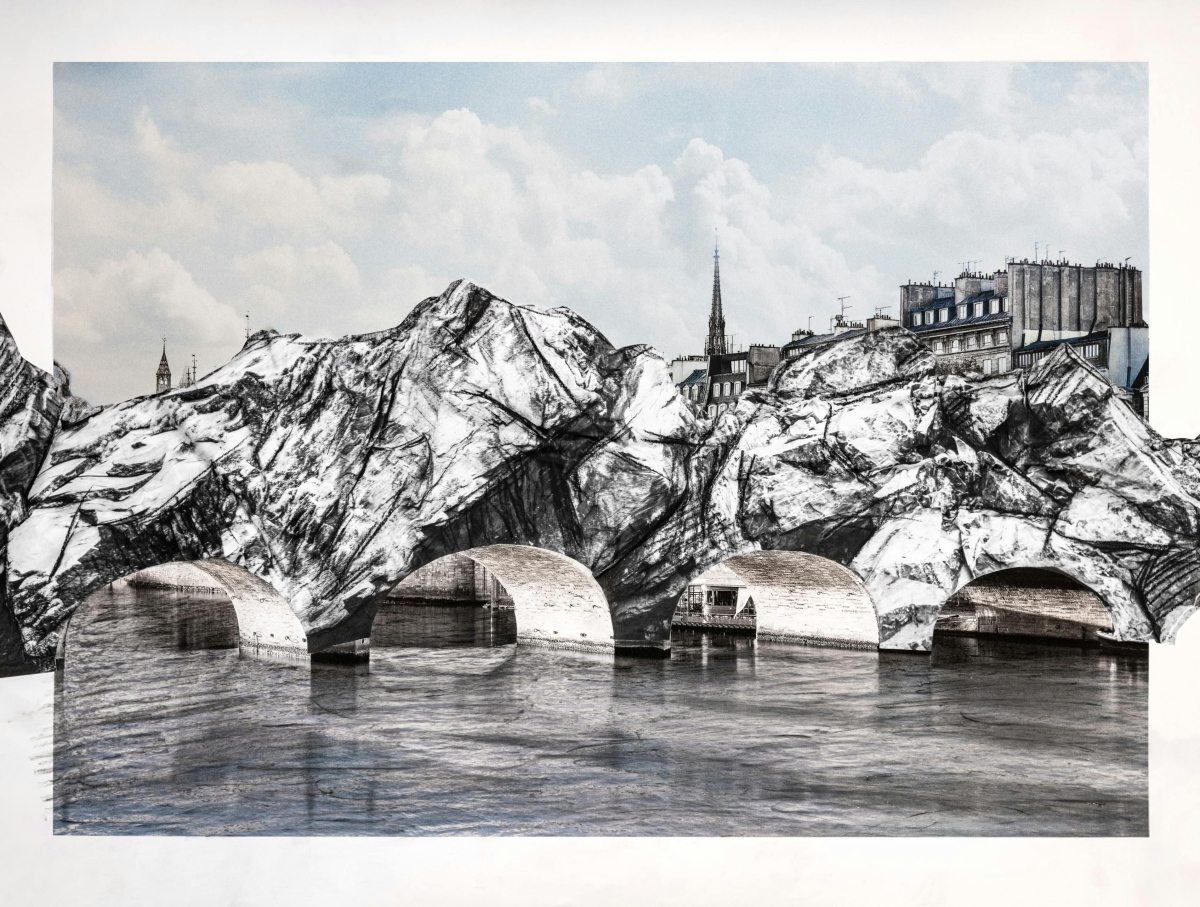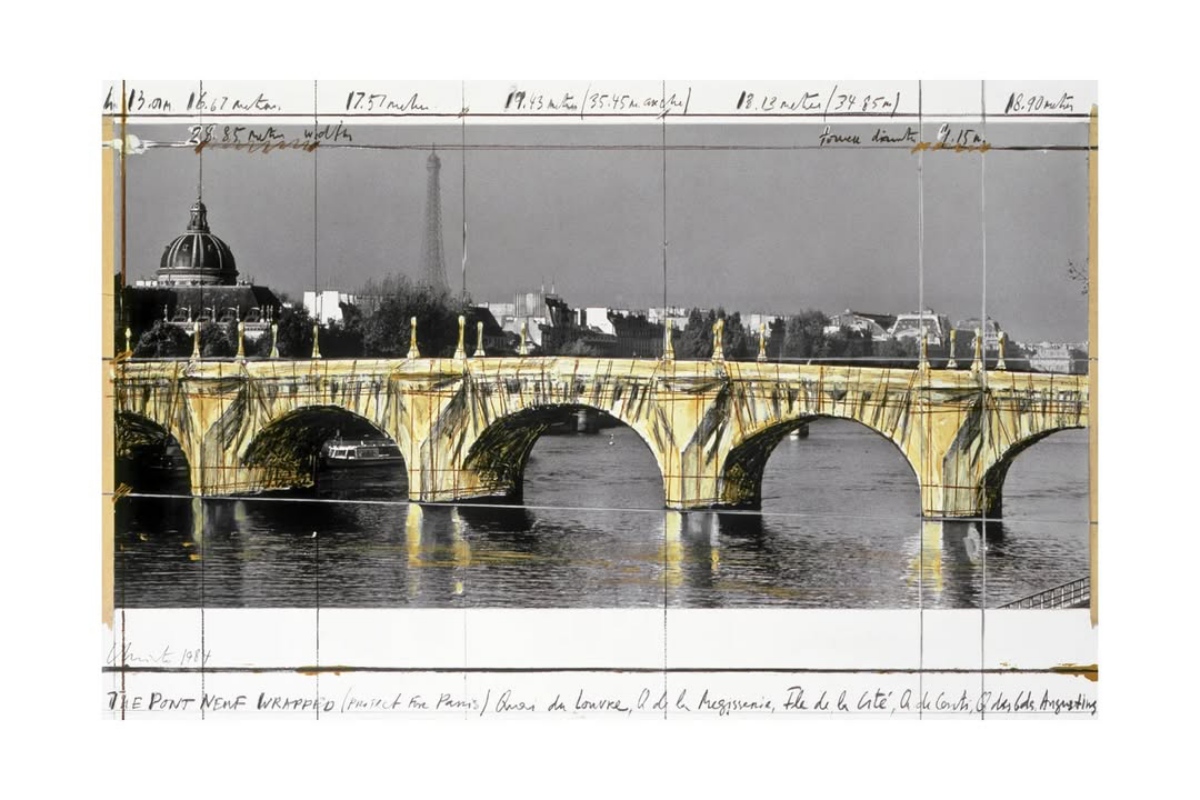導演趙德胤在電影《冰毒》中如實呈現緬甸社會的生存困境與殘酷,而在《聚。離。冰毒趙德胤的電影人生紀事》一書中,趙德胤更詳細地以自身家庭背景為例,描述緬甸華人靠著運毒、販毒的交易,試圖擺脫貧窮,得以維生。
求生不易,求好死更難:渴望勇氣、平安與溫飽的緬甸人民
在緬甸,活著並不容易。大人可能因為得罪權貴、橫死街頭,小孩子則是可能因環境衛生不好而早夭。我爸媽在雲南邊境相識、結婚,初到緬甸時,生下一子一女,長子在五個月大時因感冒夭折,若這個早夭的哥哥還活著,現在大概有五十歲了吧。之後爸媽又生了三男二女,排行老四的姊姊,在六歲時因瘧疾死亡,至於我,差點沒緣來到世間,家人為我起了小名Midi,「咪」有微小、不起眼的意思,希望老天爺可以放過這個不起眼的孩子。
因為環境艱困、醫療落後,每個緬甸孩童幾乎都在病魔的死亡陰影下長大,尤其在臘戌合格的醫生不多,診所都是一些沒畢業的醫學生,開的處方多半是給病人打點滴,補充營養,可是針劑的成分往往來路不明。此外,在緬甸看病也不便宜,現在看一次診得花緬甸一萬元,大約折合台幣三百五十元,以當地收入水準來看,如果家裡有人病上一星期,大概就會散盡家財了。所以,多數人採用偏方或買成藥治病,我猜想,是不是因為不明藥物吃多了,緬甸人多半牙齒顯得發黃。
在我小時候,小孩子光是得個感冒就可能會死人。
不知道為什麼,在臘戌感冒時的症狀特別嚴重,我們可能早上上學的時候,人還好好的,下午就開始拉肚子、嘔吐。回到家後,爸媽通常會先幫我們刮痧,利用自體發熱讓身體產生免疫力,如果情況沒好轉,小孩子開始發燒、筋骨痠痛,甚至痙攣,父親才會再用草藥熏灸,讓我們吃消炎藥,必要時注射抗生素等針劑。
和一般人相較,家有習醫的父親已是幸運,但還是免不了九死一生的染病經驗。我所了解的毒品問題,向來不是單純的是與非,黑或白的問題,而牽扯了政治、社會階層,以及求生出路的抉擇。
至於,值不值得為這個抉擇坐牢、賠命?
只能說,在底層生活的窮苦人,沒有選擇的權力,而靠著毒品致富的有錢人,則沒有拒絕的勇氣。從小到大,毒品交易就存在於我的日常生活中。
農人把鴉片當做價格稍好、銷路順暢的「經濟作物」;運毒的人也不過就是毒品「宅急便」,賣毒品的,就跟賣糖果、餅乾的,沒什麼兩樣。種毒、運毒、販毒,就像種稻、運米和賣米一樣,在緬甸很稀鬆平常,只是升斗小民較好謀生的一種方法與途徑而已。
我的家人都有吸毒、運毒的經驗,最先是爺爺初到緬甸時開鴉片煙館,他自己就會抽點鴉片煙,我父親有哮喘病,也抽鴉片。後來政府宣布,禁止鴉片館營業後,爺爺、奶奶頓失收入,我們這一房也被迫搬離了三代同住的房子。靠著父親行醫和母親做小生意,又要上繳家族公庫,又要維持自己的生活,我們家常常入不敷出,甚至繳不出房租。
好在,母親在市場做生意時,結識了一位客人許大媽,她賞識我母親做事有條理,就讓母親當管家,我們也可住進她的大宅院裡,才免於露宿街頭。
記憶中,許大媽是個寡婦,但她擁有整塊近千坪的土地,上頭蓋了幾棟大房舍,雖然都是茅草屋頂卻很扎實。說來,許大媽除了是我家恩人,也救了我的小命,因為母親當初懷我時,已經是第六個孩子,家境實在辛苦本來決定墮胎,是許大媽加以勸阻,我才能來到這世上。
一個寡婦怎麼會如此富有?原來許大媽做的是毒品大盤,大概就是「毒梟」等級。有好幾次,軍警跑來抄家檢查,許大媽也常被抓去關。
母親和幾個幫傭的中年婦人,也曾被許大媽差派運毒,她訂製了可堆疊的鐵製便當盒,裡頭裝滿了毒品,讓這些婦人們搭四天火車,送到邊境城市密支那。我媽第一次運毒成功後,得到的酬勞是兩大袋白米,許大媽私底下還特別多給我家一些食品。
當這種毒品快遞,能賺取的就是一點米糧,但是要冒的風險卻很大,一旦被抓,可能得面臨重刑。母親第二次運毒就被逮捕了,還遭判刑入獄,那年我五歲。好在最後因為政府大赦,關了兩年母親才終於回家。直到現在,中緬邊境仍有許多像母親當年那樣,單純為了補貼家計,鋌而走險做跑腿工作的婦女,她們礙於生活壓力,在知情或不知情下成為毒品行業的一員。
我從不隱諱母親曾有的販毒經歷,也不在意別人可能加諸的有色眼光。因為在緬甸許多涉入販毒、運毒的人,特別是婦孺,多數是在艱困的環境中,很勇敢地去做一件試圖讓家庭溫飽的工作罷了,他們根本無法因此而榮華富貴。
有時候我會想,在這個篤信佛教的國家裡,這些人在佛祖面前吸毒時,會不會覺得自己是有罪的?還是他們只是單純地覺得很好玩?原本,我試著在《冰毒》中,安排了一幕主角在佛塔吸毒的戲,結果幾次下來都拍不好。我想,或許是因為佛祖不允許,加上拍攝時天色已暗,最後就放棄了。
其實,在某個層面上,毒品和宗教,都是緬甸人心靈空虛的安慰劑,只不過毒品是暫時麻痺,而宗教是修行提昇。尤其是到邊境礦場挖玉的人,他們因為家貧而冒險到礦場一搏,希望以此一夜致富。但在礦坑裡的工作環境惡劣,坑道隨時有坍塌危險,再加上玉礦區時常爆發戰爭,富貴與死亡,常常就在一線之隔。
- 本文節錄自趙德胤《聚。離。冰毒》一書 -
延伸閱讀:《聚。離。冰毒趙德胤的電影人生紀事》- 摩托車 緬甸資產階級象徵
延伸閱讀:《聚。離。冰毒趙德胤的電影人生紀事》之三 - KTV 緬甸人的歌唱故事
圖文提供/天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