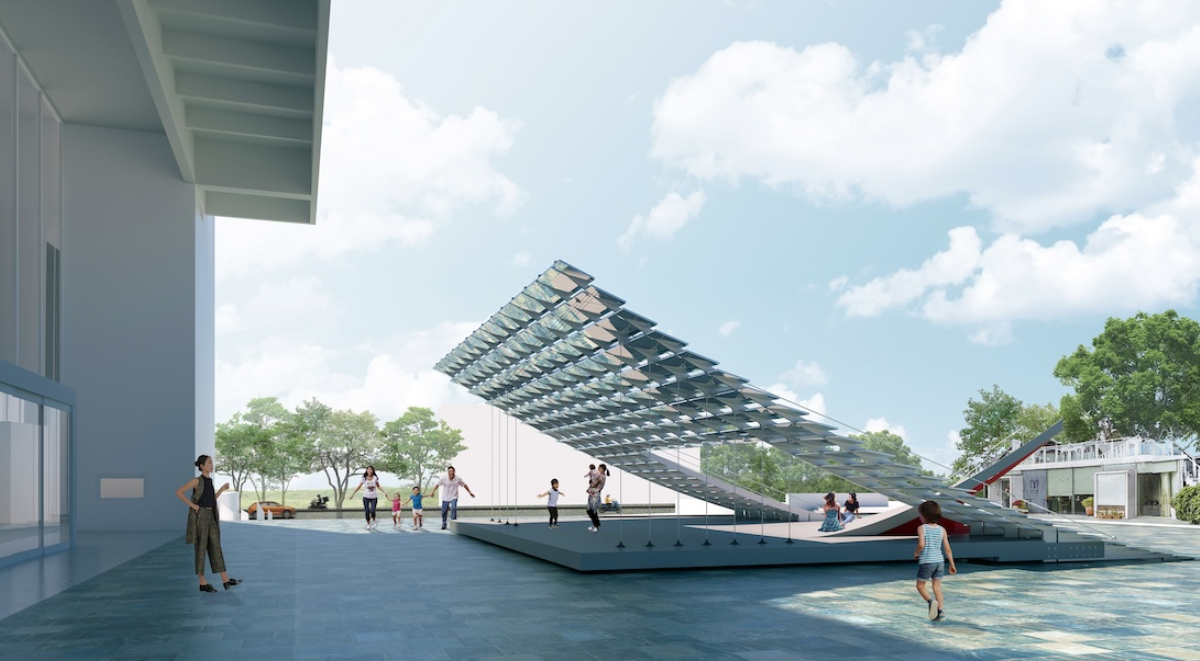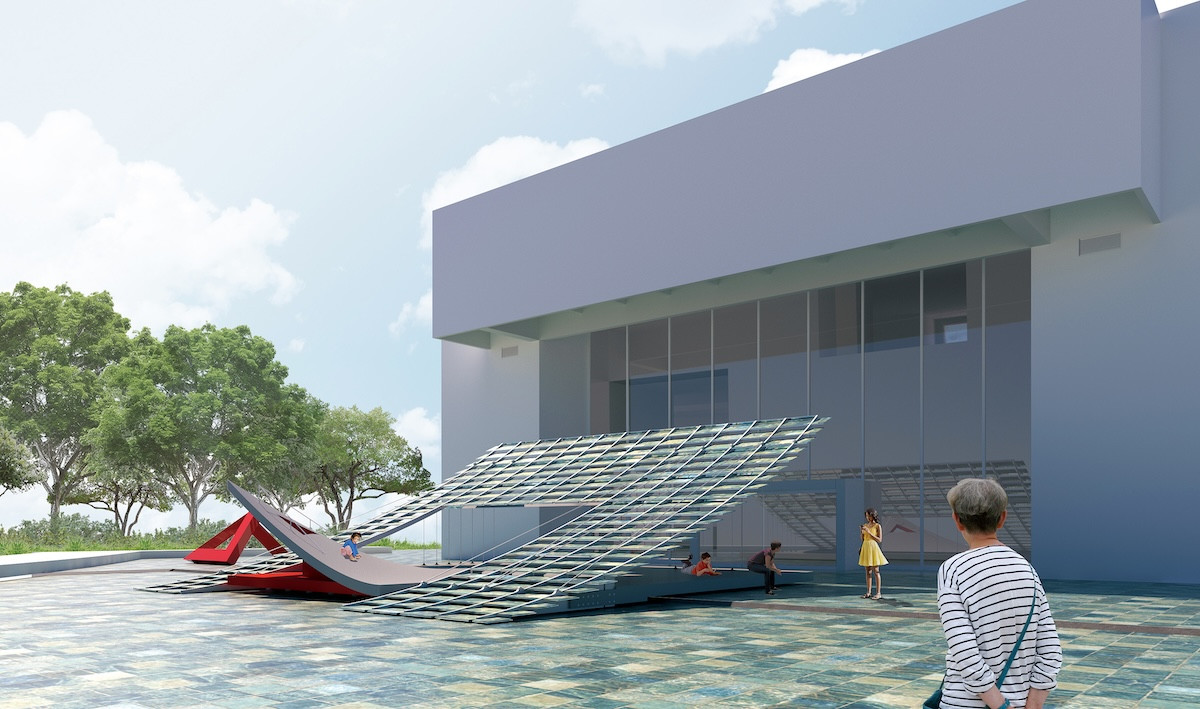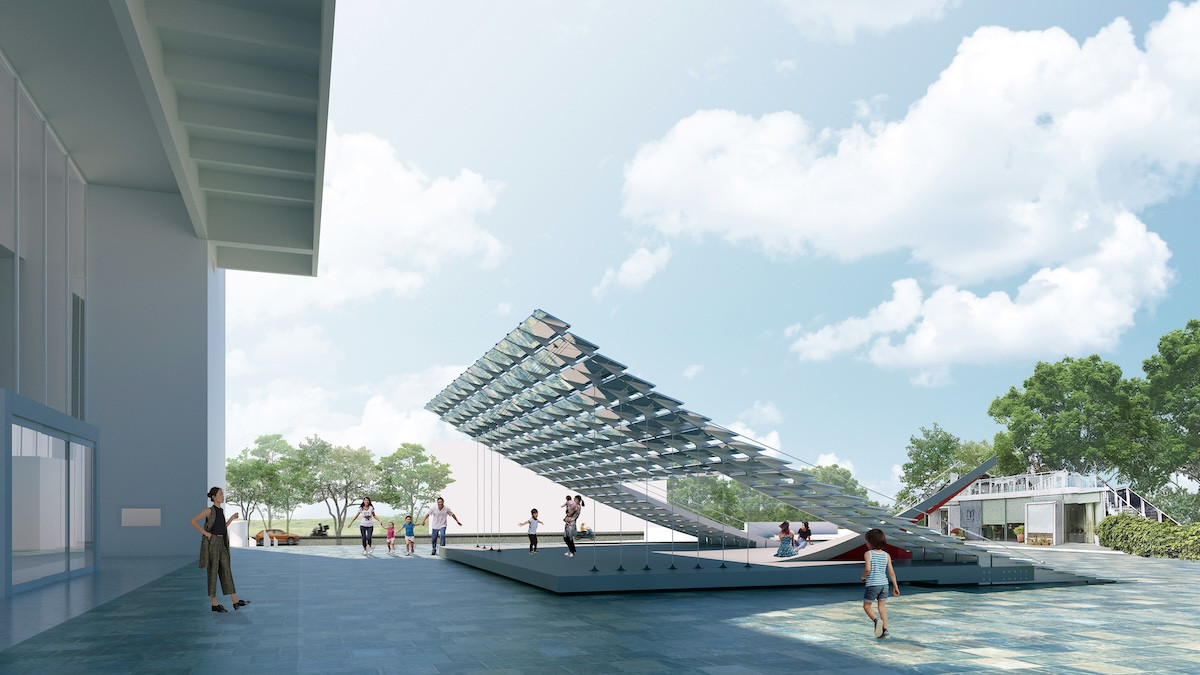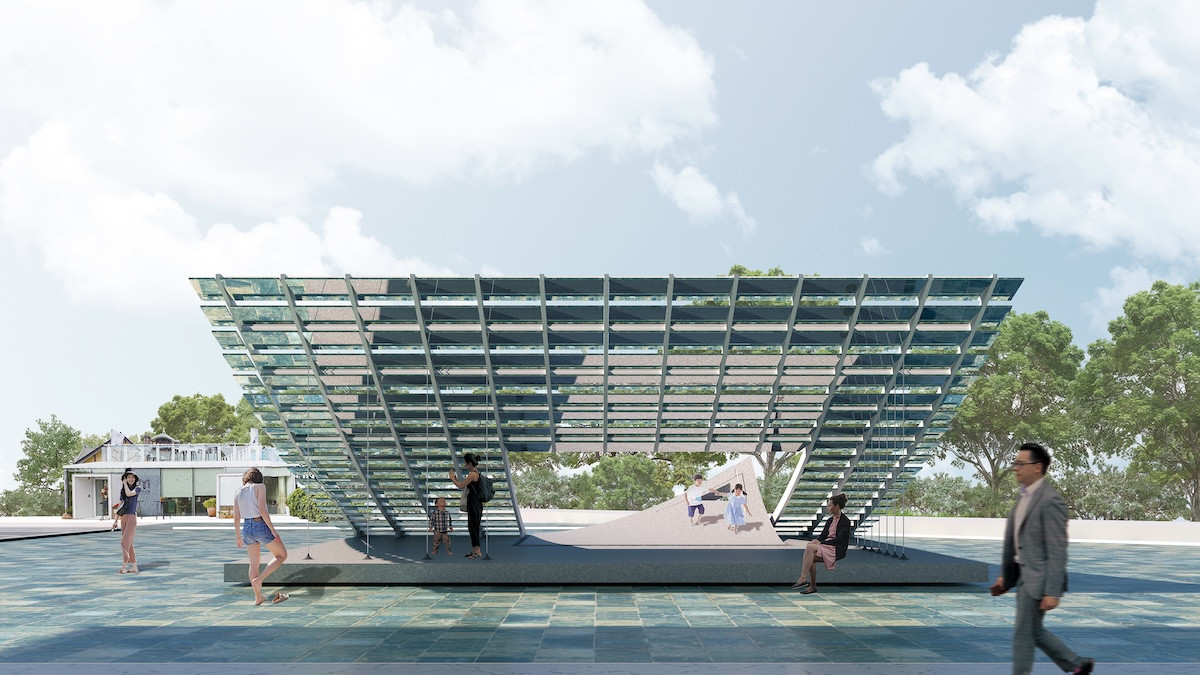跟著瑞絲薇斯朋壯遊太平洋屋脊
《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挑戰極限的自我探索與療癒
《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描述女主角雪兒史翠德從一位毫無經驗的健行者,挑戰莫哈韋沙漠沿著崎嶇的太平洋屋脊步道一路走到美國太平洋西北岸,一段瘋狂又精疲力竭的人生歷練。這一段路從墨西哥國境延伸一路穿越美國國土一直到加拿大,太平洋屋脊(PCT, Pacific Crest Trail)是一條長達4200公里的超長徒步路線,平均必須花費四到五個月才能走完全程,途中會經過「優勝美地」、「國王谷」、「拉森火山」等著名美景,是健行客們嚮往的朝聖路線,這條路線也是《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主角雪兒找回自己的壯遊之路。有人看完雪兒史翠德的《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後,毅然決然走上這條探索自我的路程,被大家公認為勇敢的代表。許多網友也被雪兒的故事感動,書中告訴大家長途健行的中心圍繞在人與大自然之間,把人類從文明生活中抽離,把所有生存所需要而不是想要的東西背負在身上,腳踏實地感受物質生活之外的生存方式。
走過四季路途艱辛 學會如何獨處、與陌生人共患難
1,800公里太平洋屋脊步道之旅 雪兒史翠德:「每秒鐘都有想放棄的念頭」
《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女主角雪兒在旅途中面臨了飢渴、炎熱、酷寒、野生動物等所有她最大的恐懼,最後她勇於面對改變,以突破自我走出一條擺脫傷痛和糾結過往的動人故事。真實故事女主角雪兒也坦承,在太平洋屋脊步道上健行94天超乎她自己的體能所及,「但這是一趟極度啟發心靈的旅程,當時我感到失落絕望,並處於躊躇不前的狀態中,如同許多人進入荒野,我選擇踏上這條艱難的步道,在許多層面上看來,我再度學會如何邁出步伐。」
每天清晨起床將自己的帳篷等物品背上身,健行PCT的路上只能帶著極簡單的行囊,帳篷、睡袋、口糧缺一不可,但過多的行李只會增加自己旅程的負擔,一如《那時候,只剩下勇敢》中瑞絲薇斯朋一開始被稱為「怪物」的行囊。所以PCT上每間隔一段路程就會有一個補給站,可以事先將自己需要補給的物品裝盒寄到補給站,旅途上也會遇到許多共行的夥伴互相幫助。PCT因為地形關係,路途過程常常會有極端的氣候,從乾旱的沙漠到滿山的雪景,不僅考驗健行客們的身體負荷,也挑戰他們的心靈勇氣。雪兒史翠德在《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裡直言「我每幾秒鐘就有想放棄的念頭」,然而在路途上遇見的人、事、物成為他繼續走下去的動力。被雪兒深深啟發也踏上自己壯遊之路的網友,在旅程中也因此不斷思考自己的人生,與自己獨處的過程中,才真正了解自己,感覺如同重生一般。
《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挑戰拍攝極限之美
太平洋屋脊步道具有美國西部粗曠魅力的形象,橫越25座國家森林和7座國家公園,海拔可達一萬三千英尺(近四千公尺),並在哥倫比亞河處深達入海,途中包括多樣又獨特的地域,例如莫哈韋沙漠、紅杉林國家公園、土歐魯米草原、胡德山和瑞尼爾山的火山地形、火山口湖的森林,一路到眾神之橋-從奧勒岡州進入華盛頓州橫渡哥倫比亞河的懸臂橋。
導演尚馬克瓦利在拍攝《那時候,只剩下勇敢》時選擇追求全新真實之美,他表示,故事是描述一個身在荒野中的女人,所以必須在荒野中實地拍攝,「我們盡可能地在太平洋屋脊步道上和鄰近地區取景,但我們一直在尋找雪兒筆下的那種美,盡可能地提早拍攝以捕捉日出,也盡可能地越晚結束以抓住日落。」尚馬克瓦利每一件事都強調忠於真實,因此全片多數時間都在戶外拍攝,在荒野中、寒冷中,或炎熱中,都非常有挑戰性。有些地點甚至偏僻到必須租借驢子或馬匹來載運裝備,但一切都很很值得,執行製片納森羅斯說:「火山口湖是無法複製的,還有好幾個具有象徵性的地點,是我們必須就地拍攝的,這些地點都不可能使用綠幕特效,眾神之橋則是雪兒故事中的情感高潮,絕對要真實呈現。」尚馬克瓦利的堅持和全劇組的努力沒有白費,《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完美呈現女主角破繭而出與大自然真實之美的每個動人時刻。
瑞絲薇斯朋深受感動 出資拍攝《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
正在全台熱映中的《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猶如女性版《127小時》加上《白日夢冒險王》,這本同名暢銷小說是作者雪兒史翠德的親身故事,內容充滿激勵人心的深深打動奧斯卡影后瑞絲薇絲朋,一看完書就立刻爭取改編電影的拍攝版權,主演同時身兼製片,找來《藥命俱樂部》奧斯卡提名導演尚馬克瓦利執導,與《非關男孩》、《名媛教育》暢銷作家尼克宏比合作,並找來蘿拉鄧及知名影集《新聞急先鋒》實力男星湯瑪斯薩多斯基精彩共演,也是瑞茲薇絲朋強勢問鼎奧斯卡的最新代表作,輕¬柔奏出一曲蛻變與重生的女性生命之歌。
《那時候,只剩下勇敢》故事敘述因為母親與會酒醉家暴的父親離異之後,雪兒就和弟弟與母親相依為命,三人世界雖然窮困卻感情親密,甚至母親還跟她一起上大學唸書,原本看起來生命正在起飛的雪兒卻面臨母親罹病和過世的痛苦,最後連自己的婚姻也走上殊途。年僅二十六歲,生命就已陷入死胡同,再也無路可逃。傷心欲絕的她只能揹起沉重行囊,毅然踏上一趟長達一千英哩的遙遠旅途,沿著美麗又殘酷的太平洋屋脊步道,她一步一步嚐盡了孤獨的滋味,也終於面對自己張牙舞爪的心魔。更多電影詳情請洽福斯電影官網。
圖文資料提供 福斯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