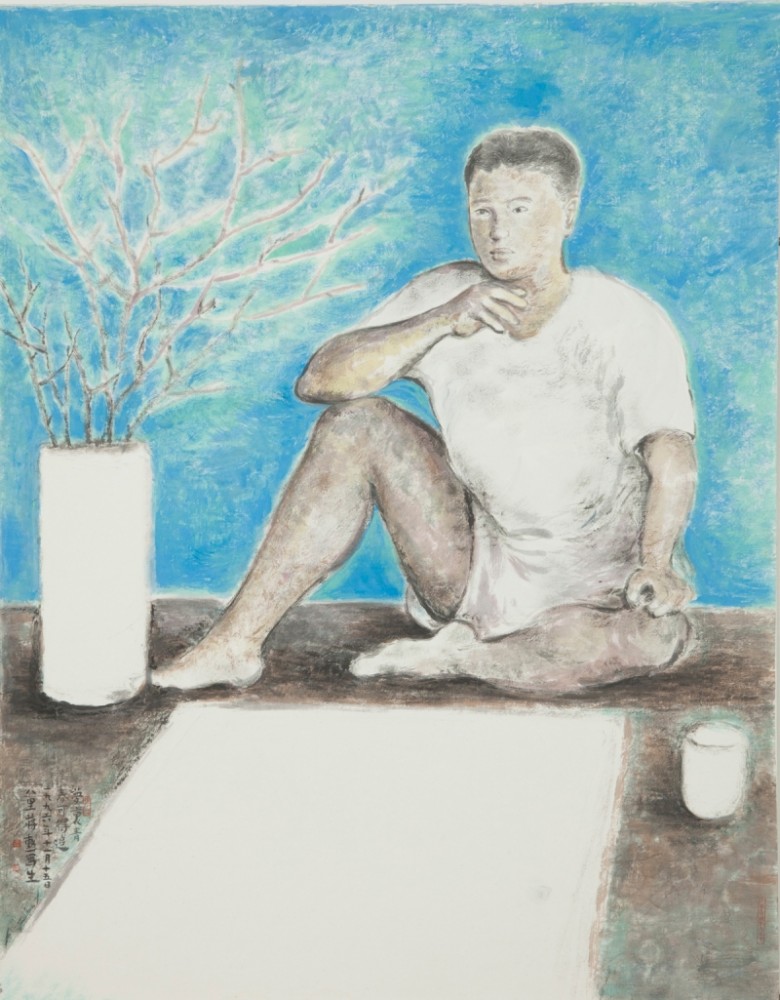每次蔣勳去行天宮附近的錄音室錄音前,總習慣繞去大龍峒廟口吃碗米粉湯,「還是老店熬的湯底好。」從小成長於保安宮後方巷弄,蔣勳懷念的不只是慢火細燉的滋味,還有高度工商業化前,看得見星空月光的光環境。
50年代的台灣,還是節儉的農村社會。蔣勳說,現在的年輕朋友恐怕很難想像,小時候家家戶戶最普遍的光源是蠟燭和油燈,儘管家裡也有電燈,但幾乎得隨時關燈,否則就會被父母責罵。就連當時比較有照明設備的廟宇神龕,光線也都是壓低不刺眼的。
遠離人造光 重回自然光環境
正因當時對物資的珍惜,日常環境中反而可以感受到多種自然光。小時候蔣勳從家往西北邊走就是淡水河,往東就是基隆河,沿路上一直能感覺到河水的光,「記憶中河裡有黎明、夕陽,還有月光。」
「我很懷念那個年代,大家曾經擁有光的美好記憶。」在七巧節的晚上,蔣勳的母親會在院子裡講牛郎和織女的故事,母親指著天上的銀河,帶著孩子們辨認織女和牛郎星,一邊讀著唐詩,「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文學跟自然環境竟也能完全的融合在一起,那是他童年裡最感謝的一件事。
而元宵節,蔣勳一定到保安宮排隊領燈籠,提在手中的紙燈籠,風一吹就燒起來,一下子成了一團火光。「原來人生中有一種光是這麼幽微又燦爛,卻不能永恆。」這變成了蔣勳生命裡,最強烈的美學記憶。
也許從另外一個角度,在那樣的環境長大似乎很窮,卻是拜沒有過度的人工照明所賜。然而不過數十年,看得見自然光的光環境已經徹底消失了,蔣勳心裡覺得很遺憾。現代人的情緒處於焦慮和亢奮之中,或許跟不當的光環境有關。
蔣勳相信成長於不同的光環境,對光的感受不一樣,在美學上所要傳達的東西肯定也不同。蔣勳曾經在月圓的晚上,帶美術系的學生到太魯閣玩,立霧溪的水被月光照亮,整個峽谷亮起來,美得驚人,所有的學生都呆住,有的甚至都哭了。
「夜店如果要讓人High起來,一定先閃動光,刺激人的感官。」蔣勳一直覺得台灣的人心浮動,跟長期對光害無感,沒有意識這是心靈之害有關。尤其一到選舉,高達10層樓的候選人巨幅看板,光打得亮通通的,加上宣傳噪音,非常可怕。
反觀法國、日本,連海報的尺寸都有所限制。他相信,如果有一天台灣的候選人贏得選票,不會是因為聲光壓過別人,反而是由於懂得有所節制,那意味著台灣整體的文化美學環境提升了。
減光新美學 讓奪目、絢麗退場
「醜,其實也是有慣性的。」節制對感官漫無邊際的刺激,是台灣一定要走的一條路。尤其光與聲音無遠弗屆,不是自己做好就可以,也會受到周遭環境的影響,蔣勳覺得政府應該要起來帶頭,或許在中秋的晚上不是烤肉,而是集體減光一小時,讓大家重新有機會感受月光盈滿之美。
「整合同一個區域的公共建築和街區照明,避免各事其主也是可以努力的方向。」像是新修復的國定古蹟台灣總督府鐵道部與鄰近北門照明的協調性;以及整個博愛特區的照明系統,包括總統府、外交部台北賓館、立法院、行政院、台大醫院,甚至二二八公園等,將來如果規畫好。做出示範,城市的照明從奪目退回到幽微,一定會慢慢的呼喚出很多記憶出來。
在地社區有共識也很重要,像池上的天堂路本因應觀光的需要設了路燈,但當地農民說,稻穀被24小時的路燈照射,無法休息,這已經不是池上米,最後集合一百多位農民之力反映,終於拆掉路燈。蔣勳跟龍應台曾在這裡看到非常漂亮的銀河,由此可見台灣有些地方的民間力量已經展現。
在幽微光里 找到真正的自我
「光太亮時不能談心事。」所謂光鮮亮麗,在很亮的光裡,人都是偽裝的,不太容易有真實的自己出來。
白天的光是職場、公眾的光,只有在夜晚幽微的光裡,人們才會比較靠近一些些。蔣勳說,所以如果朋友來家裡談心,燈開得太亮的話,兩個人都會處在焦躁狀態中;他也跟朋友說,「如果想跟孩子談心,餐桌的光不妨可以調低一點」,至少不要讓光直接照到眼睛,一定會有幫助。
相對於希臘神話描寫的多是太陽的光,蔣勳說東方特別喜歡的是月光,唐詩裡很多的光都是夜晚的光,所以李白說,「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詩裡頭透出的是可以跟月亮、跟自己影子對話的光,唐詩宋詞經常保留了人在夜晚做自己的難得和喜悅,所有的光都是幽微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望月懷遠〉,張九齡
適切的光亮 剛好即是最好
25歲的蔣勳前往克里特島的時候,在愛琴海夜航的渡船上頭,看到海面上遍灑的月光,想起兒時所讀過的〈望月懷遠〉,撼動不已。現在再看這首唐詩,幾乎就是一種對於光的呼喚,一種減光的呼籲。「滅燭憐光滿,不堪盈手贈」,當一個人能夠感受、憐惜月光的好,將燭火滅去,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一件事。蔣勳相信,有一天我們能感覺得到月光,甚至想用雙手捧起來送給遠方的朋友,那是人的心安靜下來,美學又回來了。
「童年有一個好的記憶,人的一生會受用無窮。」蔣勳一直覺得,兒時的記憶幫助他很大,如果說小時候讀過的唐詩,是美的庫存,可以一生提領不盡,那麼找回台灣適切的光環境,是同樣重要的。
或許那時,所有曾經被忘卻的感受性,會像他曾經看過河上的幽微月光,再度回到生活,和生活者的意識中,蔣勳對此不禁有一絲期待。
小檔案 蔣勳
作家、美學家,長期創作論述生活、文學與藝術,引領人們進入美的殿堂。今年擔任第一屆台灣光環境獎評審,出版最新著作《雲淡風輕:談東方美學》。
撰文者:駱亭伶
※本文由 商業週刊 提供,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關於光影的更多資訊,請見《La Vie》2018年12月號:光與影的生活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