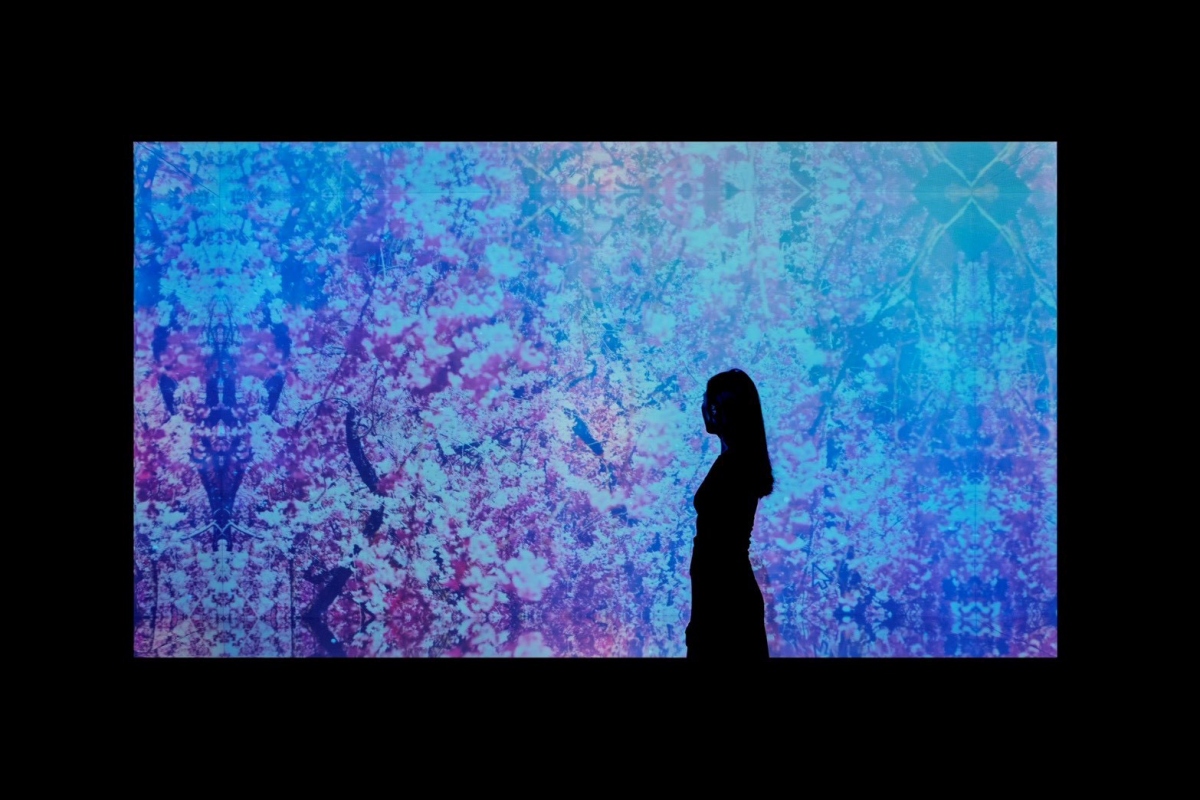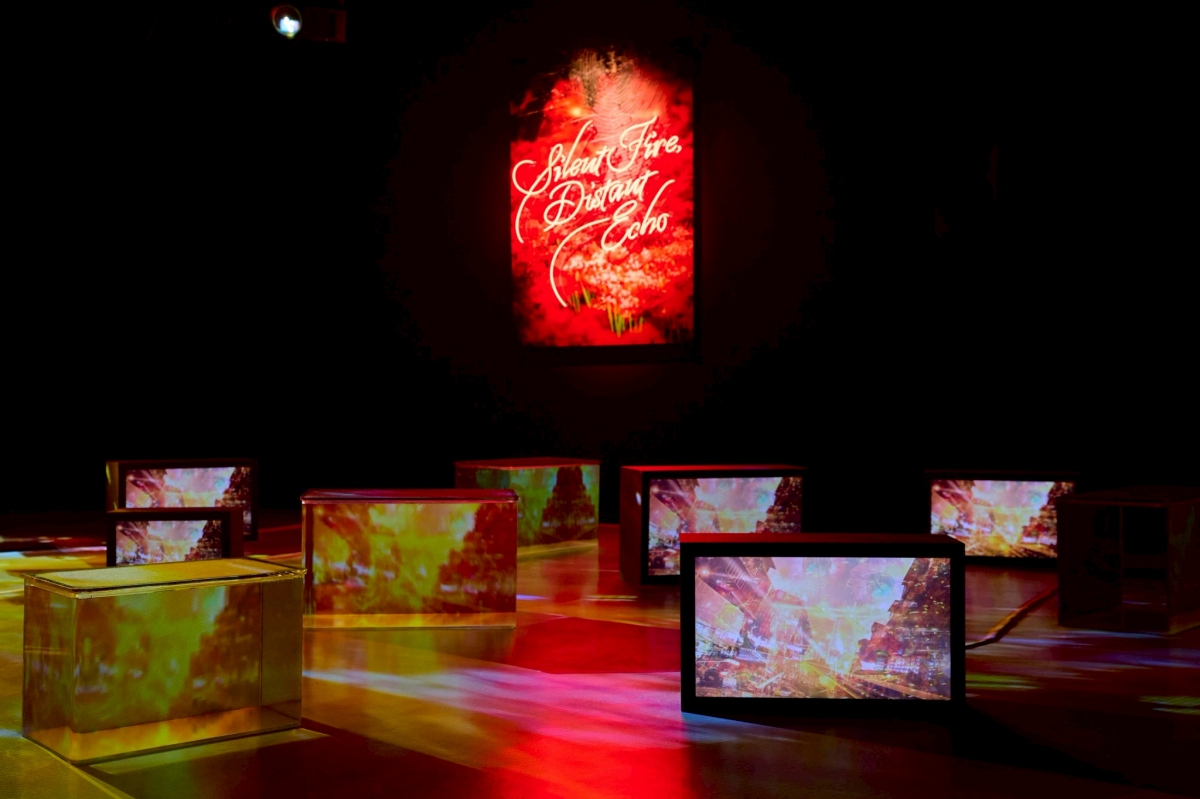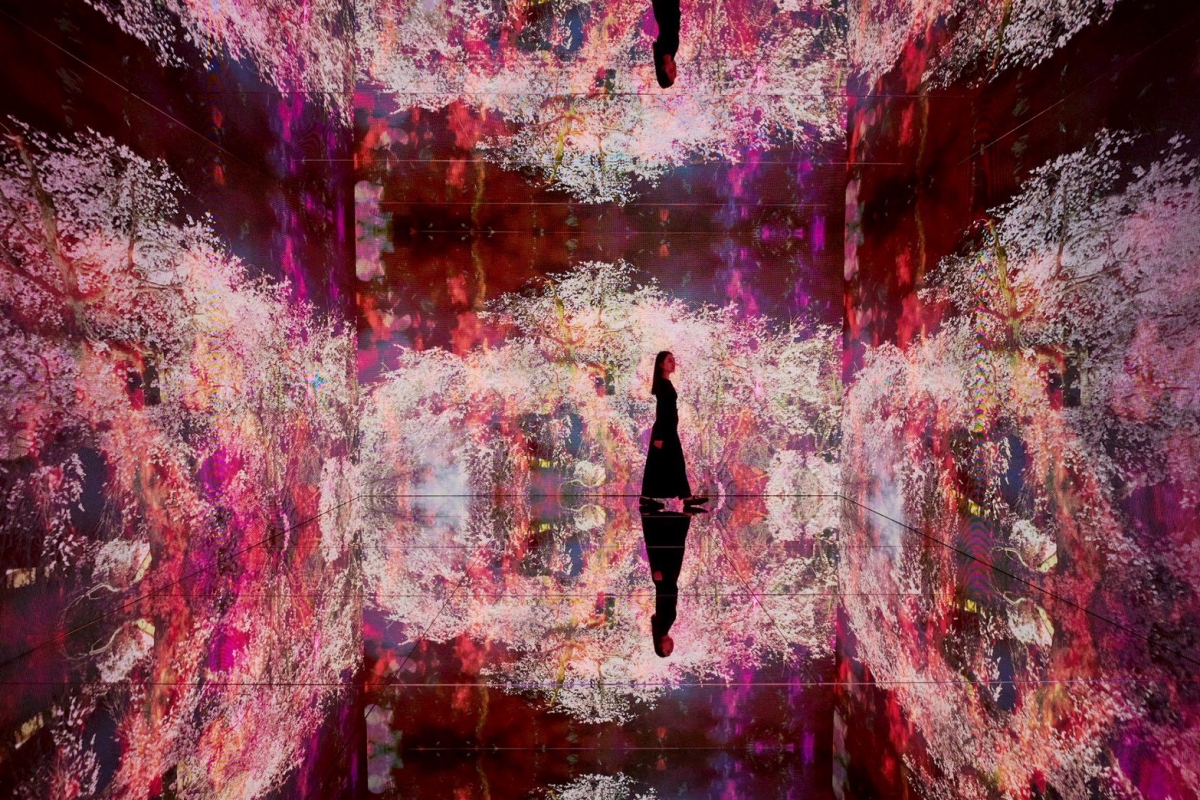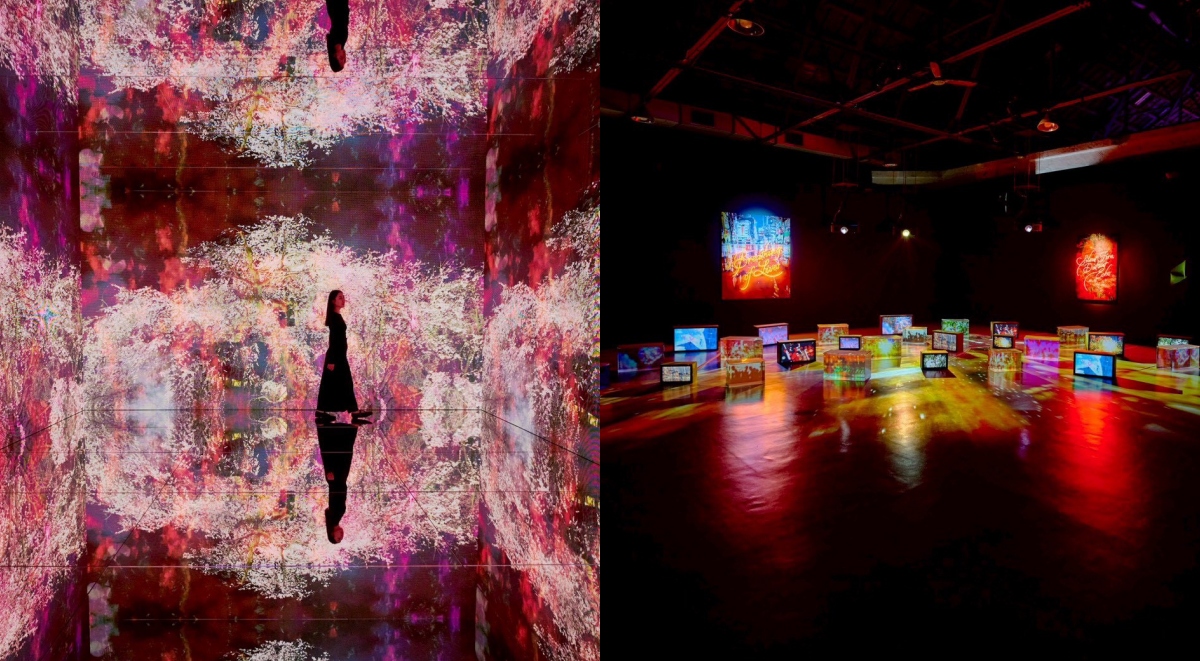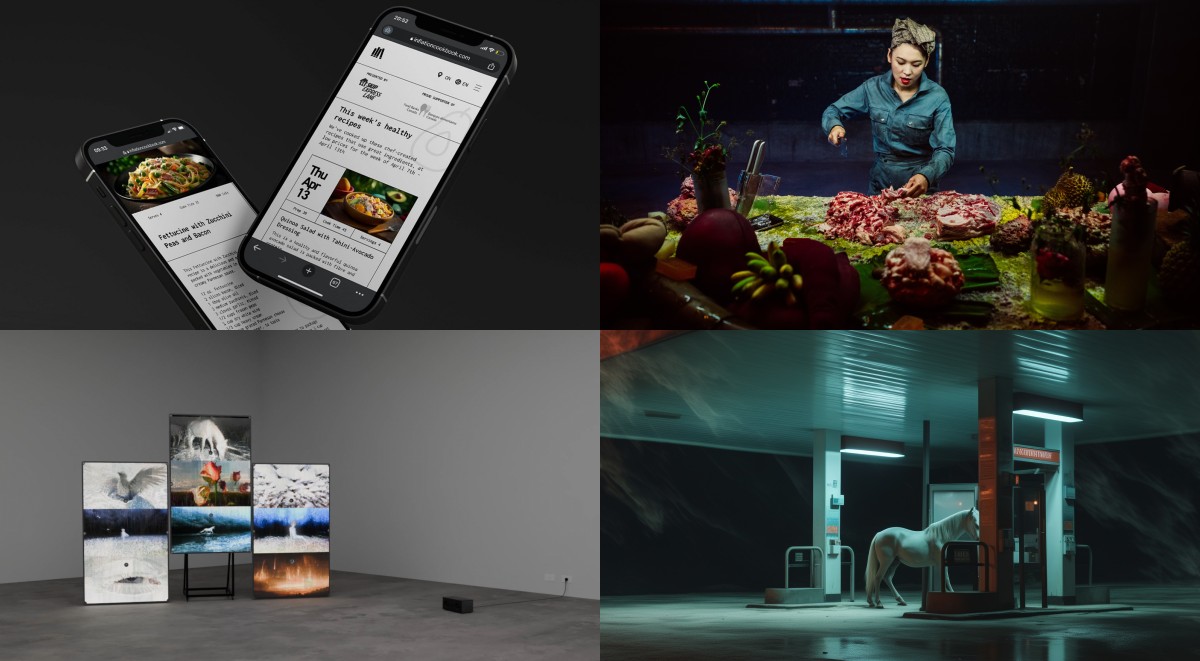「我沒病。我只是壞了。只要我還能畫畫,活著就是件開心的事。」
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出生於墨西哥市,父親是德裔攝影師,母親家是墨西哥與西班牙血統的族裔。雖然他們以墨西哥裔為傲,但她更常使用父親給她的德系名字芙烈達(Frida)。卡蘿的一生,遭遇了許多逆境,她6歲時罹患小兒麻痹,18歲又遭遇嚴重大車禍,導致卡羅無法生育,即使懷孕三次,都不能留下孩子。
由於命運多舛,小女孩在家裡有著不同的地位,父親似乎特別寵愛她,教了卡蘿很多修改底片的技巧;父親忙碌時,她也可以分擔工作。家庭環境與人生際遇也讓畫圖成為卡蘿生活中最適合的活動,她可以在醫院、在家,畫自己、畫寵物、畫植物,寓意、想像都可以,本想學習醫學的她,也因此逐漸具備藝術的能力,而成為世界知名的藝術家。
卡蘿一生待在醫院與行動不便的時間很長,這也造就她畫自畫像的經歷,她一生畫作有143幅,其中55幅是自畫像。1950年後,由於脊椎手術失敗,細菌感染後必須截肢,導致身體狀況惡化逝世。
遠觀卡蘿,可說是生命奇蹟,她亮麗驚心,才華洋溢;近觀卡羅,雖災難不斷,仍不輟不餒。我在閱讀過以卡蘿為主題的繪本後,除了發現更多關於卡蘿的繪本,甚至起心動念想前往墨西哥繼續解讀卡蘿的生平與創作。
「藍屋子」(La Casa Azul),是卡蘿在墨西哥市的故居,建於1904年,為她出生、長大、婚姻、教學、去世的主要所在,這裡從1958年起規劃並對外開放為卡蘿美術館,位於舊市區優美的社區裡,已經成為墨西哥市的主要景點了。
體弱多病的卡蘿,被呵護、璀璨、苦難的短暫生命就像一齣連續了47年的劇場,在藍房子裡不斷上演,從不重複。這同時也是時間長短相對的感受:對一位藝術家來說,我們希望她長壽些,有更多作品傳世,47 歲英年早逝;對一齣連續劇,我們會覺得夠長了,無力追劇。卡蘿的一生波折多難,身體因小兒麻痺、車禍造成的傷害,造成心靈異於常人的堅毅與需求;她在藝術領域的狂野與創新,讓觀者讚嘆。
經常有朋友對我說,「只要你真心想要的,就會有神奇的力量來幫妳。」這些心想事成的實現,經常造成特別的經驗;心存感激,覺得運氣特別好之際,亟欲分享這樣的信念給書友。
往往在旅行時遇上驚喜的展覽,遠比計劃中的還要精彩;譬如之前在慕尼黑偶然地遇見了盛大的克利與慕特的個展,在鹿特丹誤打誤撞,闖入一個地位重要的美術館,最後趕上倫敦的卡蘿展。確實這一年身歷看展的好運,也發現世界各地對藝術家的關注早已鋪天蓋地進行中。
我去訪問藝術繪本作家瑪麗安・杜莎(Marion Deuchars, 1964-)時,恰好隔天她就要前往墨西哥市,並已經預約好藍屋子的參觀。我們也聊起卡蘿結婚後,與先生分住兩個屋子,這樣one family two house的結構也成為許多獨立女性的理想。
在婚姻裡是否能夠保有自我,繼續完成自己,一直是很多女性難得平衡的觀點。生活起居需要旁人照顧的卡蘿,對這點相當執著,即使先天條件不足,她也過得像個女王。為什麼這麼說呢?一起進入繪本裡來看看吧。
Viva Frida
本書的創作者,巧妙地透過不同視角的運鏡,變化寬窄遠近的視覺語彙,帶著讀者走入卡蘿的內心世界。作者莫拉雷斯(Yuyi Morales,1968-)同樣來自墨西哥,她在手工製造的黏土布偶內藏鐵線,以固定偶型的動作,主角雖是戲偶,但書中的背景更是多所斟酌。仔細觀察每一個戲偶的細節,從髮型、服裝,即使長裙下若隱若現的腳,都有粗細之別,每個看似細微的配件都有其意義,如同卡蘿畫作裡的符號。
翻閱全書,就像在欣賞一齣精美的戲偶劇,繁複的手工嘆為觀止,精采的畫面, 卻只構成搭配少量的文字,畫龍點睛地闡述了卡蘿的生命旅程。正如卡蘿畫了許多自畫像,這段文字也有很多「I」。
I see. I search. I see ah-ha! I play. I know. I dream and I realize that I feel and I understand that I love and create and so I live.
卡蘿被爭議的情感世界、留下的畫作、甚至由法國肖像攝影師吉賽兒・弗羅因德(Gisèle Freund , 1908- 2000)為她拍攝的攝影集,都是女性藝術家的經典代表。書本一開始就出現的鳥,傳神地回應她生平名言: 「如果我能飛, 為何需要腳?」作者更以卡蘿的臉,呼應那幅被射了許多箭的鹿頭畫作《受傷的鹿》,或許對繪本創作者、藝術家而言,生命不是隨著呼吸延續,生命由作品延續。
Me, Frida
正當多數的繪本都以卡蘿的一生為題時,只有這本書講述的是卡蘿在美國的經驗。此繪本的創作者肯定非常領略卡蘿的生平,才能做出如此精萃的作品,如果你有機會多了解卡蘿的生平、日記等相關文獻記載,觀看本書時,一定會更被創作者投入的心思所感動。
書本的主要時間軸是卡蘿與先生迪亞哥・里維拉(Diego Rivera, 1886-1957)到美國舊金山發展的期間,書中詮釋了當時仍依附著先生的卡蘿,由於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加上思鄉,因此出現許多不適應的心情。里維拉當時已是墨西哥知名的壁畫藝術家,是卡蘿習畫的老師,更是卡蘿兩次結婚的對象。里維拉的故事也很傳奇,里維拉其實是雙胞胎,但生產時卻只有他存活下來,由於從小體弱,父母便將他送到山裡由專人照顧。
在森林裡長大的他,再次回家時已長成了強壯的孩子。他體型壯碩、大手大腳,不習慣坐在教室的生活,卻非常喜歡畫圖。父親為他準備畫室,沒想到他卻畫在家裡每一面牆上。長大後的里維拉也曾到歐洲深造,並將墨西哥的生活作為壁畫主題,以此成名。里維拉與卡蘿體型差異懸殊,卡蘿的父親就比喻他們倆像是大象與鴿子。
1930年,里維拉應邀到舊金山繪製城市壁畫,這也是卡蘿第一次離家。當時里維拉已是各界的關注焦點,卡蘿則因為頓時失去從小以來的特別呵護,開始勇敢地探索舊金山,並畫出自己的作品。
卡蘿與里維拉兩人觀看世界的方式不大相同, 生活節奏也不盡接近。好強的卡蘿,從小就是家人的目光焦點,因此對於自己的標準極高,要做就一定要表現到最好,但當時藝評家對卡蘿的畫作卻僅給予普通的評價。直到她畫出《芙烈達・卡蘿與迪亞哥・里維拉》這幅畫,作品中充分運用了墨西哥的色彩,並放進鴿子與彩帶,透過自己與里維拉體型上的對比,隱喻心中感受,卡蘿正式開始建立起自己的風格。
Frida Kahlo and Her Animalitos
熟悉卡蘿作品的人都知道,卡蘿經常在創作中加入箭、荊棘與動物等圖像作為隱喻。動物可說是欣賞卡蘿作品的必要元素,而本書的作者便是深入研究這些在不同時期,出現於卡蘿相片與創作裡的動物。或許可以說,本書打開了另一扇認識卡蘿人生的門。
卡蘿從小便養過許多寵物,開始畫圖後,也因為行動限制和自我內省,畫了許多自畫像。在這些自畫像中,就經常出現動物陪伴在側,有小鹿、黑貓、猴子、驢子、老鷹、火雞、狗、鸚鵡。
這些動物依序出現在卡蘿的生命時程,也出現在她的畫裡。不論是動物們所代表的個性或是精神,都陪伴著卡蘿,並給予她靈感和力量。而這些被允許隨意走動的動物,彷彿代替了行動不那麼自由的卡蘿。
除了小動物,本書對於卡蘿造型的描繪,也非常細心。卡蘿的外型特殊,在電影、其他書籍裡也都使用她的一字眉讓觀眾易辨識;而本書除了眉毛,還留意不同年紀時的髮樣與造型。據說卡蘿每天要花很多時間梳妝自己,包括服裝、髮型、配件、化妝,徹底實行「每天展現最漂亮的自己」的精神,即使不出門也是風格打扮。
繪者在書中的許多細節,採用了溫和但殘酷的描述筆觸。譬如卡蘿罹患小兒麻痺後,學著同齡的孩子騎腳踏車,當時她也喜歡扮男裝。中學時,好強的她與男孩們一樣,騎著驢子,但明顯地看見雙腳不同粗細。為了表現那場讓她支離破碎的車禍,繪者放了把火在她身上,搭配公車翻覆和骨頭分裂的畫面,暗示幾乎無法生還的災厄。先生為她蓋了一個金字塔型的寵物遊樂區,也暗示著婚姻關係中隱藏的難題。最後當卡蘿躺在床上,一旁放著輪椅的畫面,提醒讀者,卡蘿人生中最後一次個展開展時,她是躺在床上,由醫護相關人員抬著床進場的。看似輕描淡寫的頁面,卻帶過她人生的重要經歷,每一次的翻閱,都深深地打動讀者體會卡蘿人生中的偉大磨練。
Frida
由西班牙藝術家安娜・胡安(Ana Juan, 1961-)所繪、2002年出版的Frida ,可能是最早開始關於卡蘿的繪本;封面那位乘在紅鳥上畫著紅鳥的一字眉卡蘿,清楚點綴出這位二十世紀重要女畫家的魔力。其他常見繪本還有法文繁複紙雕做法的FRIDA ,與Frida et Diego, Au Pays Des Squelettes ;電影《可可夜總會》也在墨西哥的節日「Day of the Dead」裡提到卡蘿。
「Day of the Dead」是墨西哥的習俗,他們認為人的死亡分三種:去世之後有人想念的、去世之後沒有人想念的,最後一種是雖然尚在人世但沒有人想念的。每年十一月一日,有些地方從十月三十一日就開始跳舞慶祝,隔天將這些食物帶到墓園與死去的親人分享,如果是年幼去世的就第一天過節、如果是成人才去世的就第二天才過節。聽起來很類似我們的清明節,但是歡樂氣氛較濃。而且依照習俗,大家會用紙漿做各式各樣的人偶慶祝;鮮花、蠟燭、食物是必須的,以歡迎回訪的靈魂,其他如舞蹈、儀式則視當地而定。
這樣對生命的紀念與實踐的方式,漸漸地傳達到世界各地,在我們珍惜當下,也珍惜彼此之間的情份思念時,生命的價值自然延續,沒有意義的自然被淡忘。對一般人來說,現在卡蘿的知名度遠大於里維拉,一定不是他們預期得到的。
Frida Kahlo: The Artist who Painted Herself
Getting to Know the Greatest Artists 系列裡的這本卡蘿專書,以相片、圖、漫畫分別陳述了當時生活如何對應卡蘿的作品。這系列繪本的特色,內容簡單富有童趣,彷彿小學生寫報告的圖文書,也一直是藝術家入門的最佳讀物。本書中便舉列許多卡蘿不同年紀時的代表作,讀者可以快速連貫與回顧。本書的作者將主角的名字命名為「Frieda」,以呼應卡蘿的德裔原名Frida。事實上,為了抗議希特勒迫害無辜的百姓,卡蘿後來宣布不再使用她德文的名字。
文字:賴嘉綾
欲知更多藝術家故事,都在La Vie叢書出版 《懂得欣賞,是件快樂的事!聽故事、入門藝術、逛美術館,美感探索的繪本提案70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