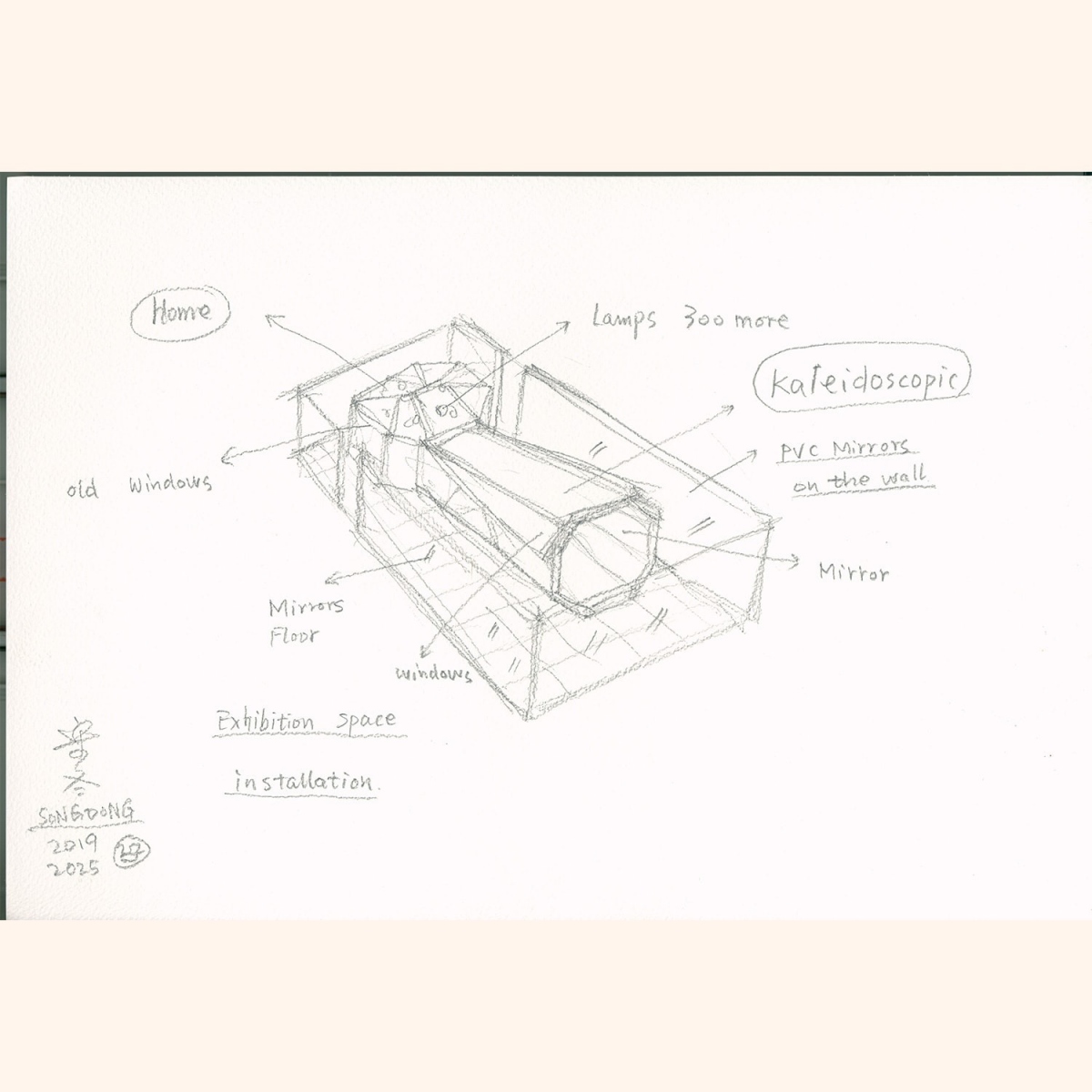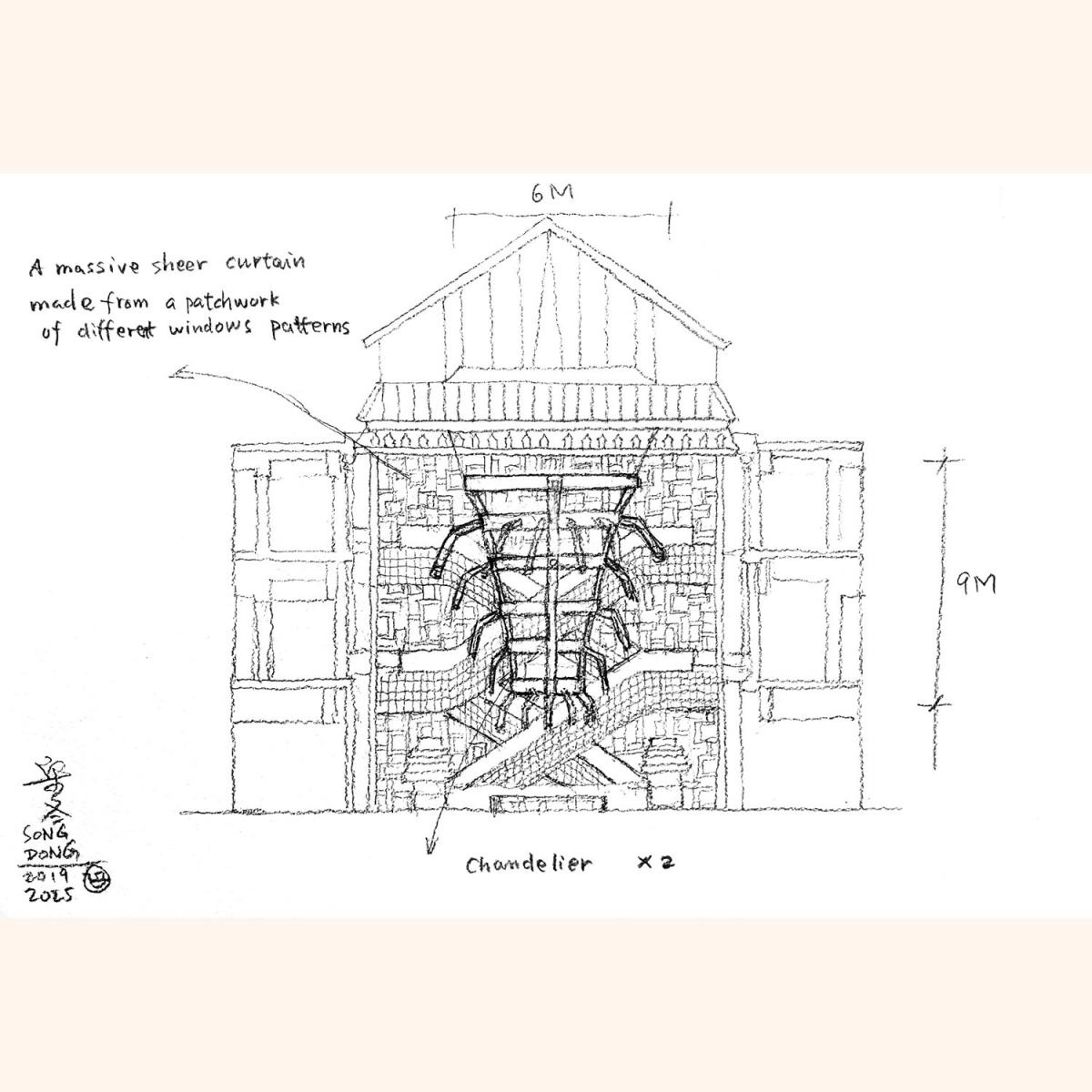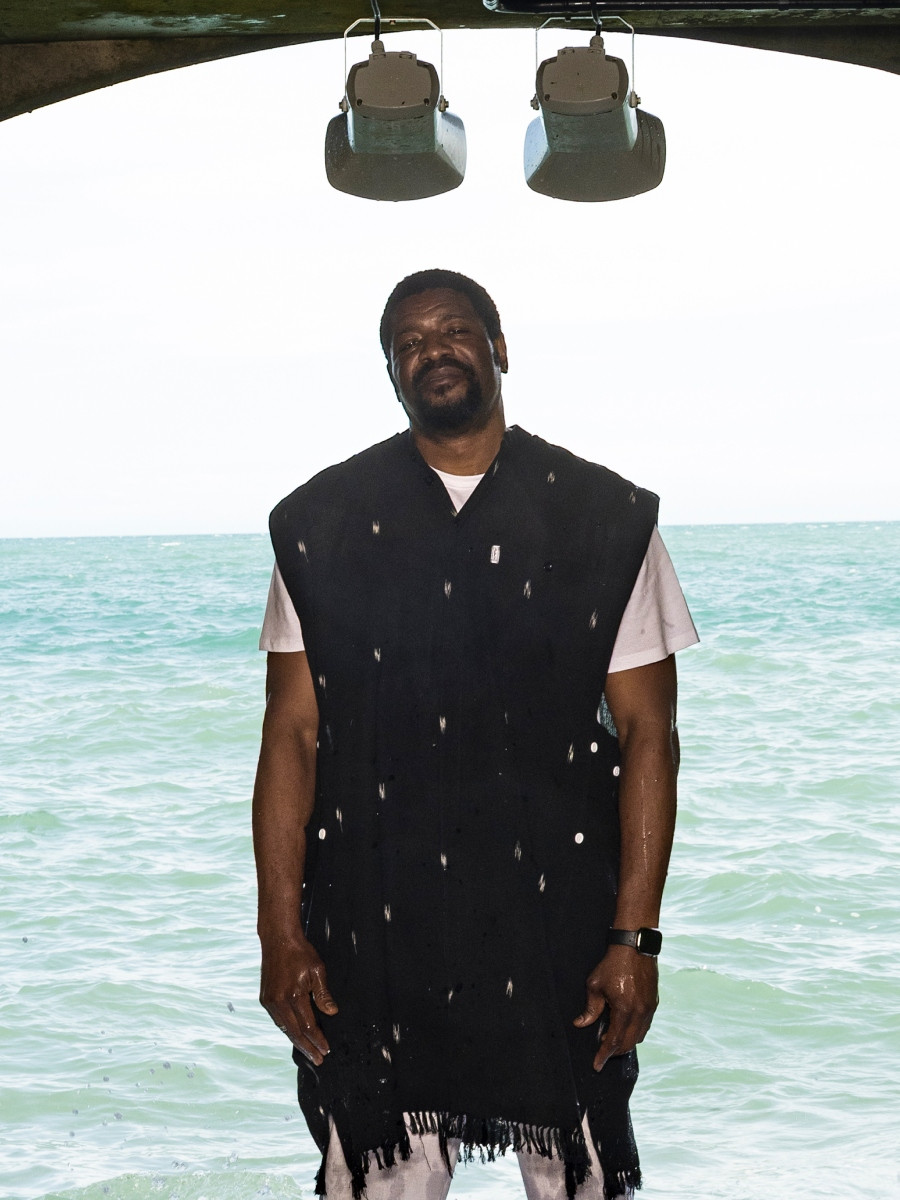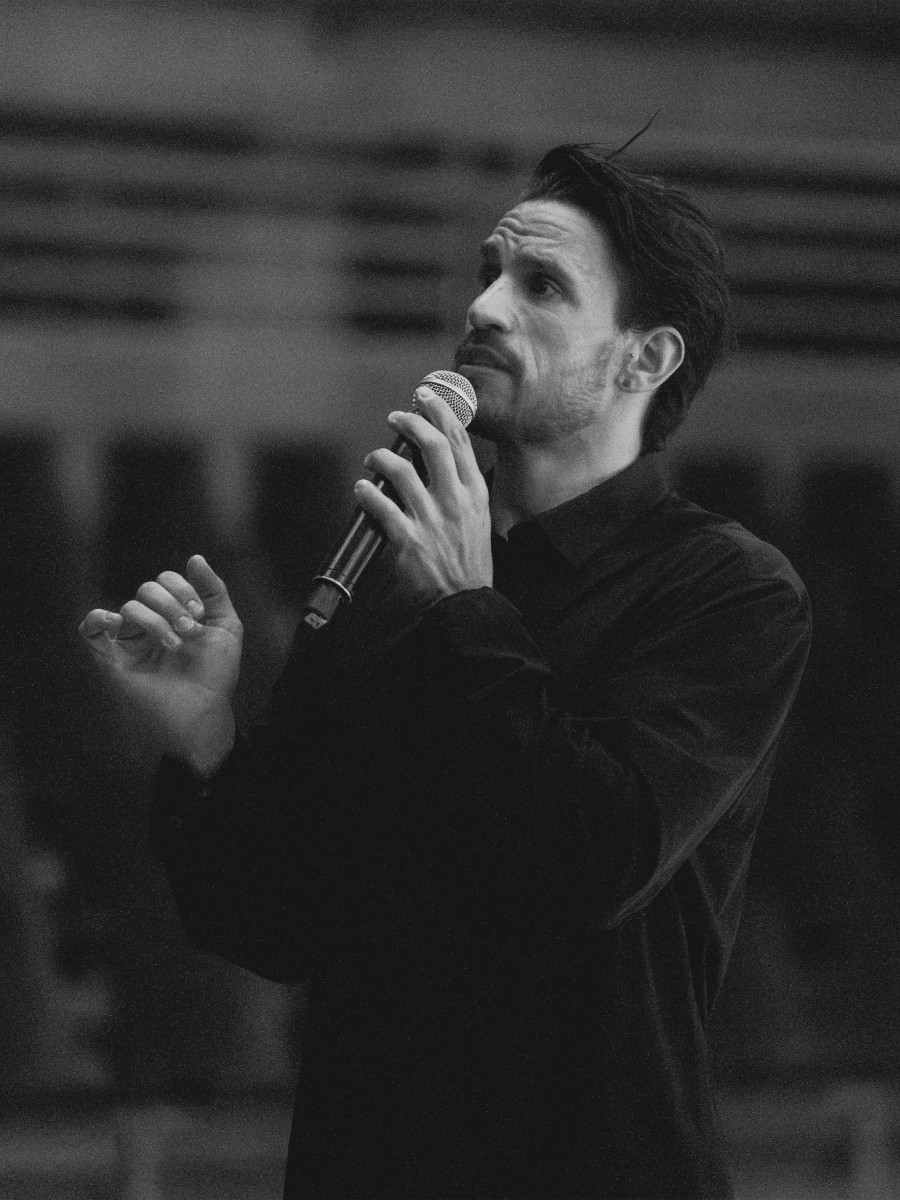2022年3月,瑞典設計師Christoffer Jansson於Instagram上發布了一則「喬遷新居」的貼文,宣布購入一間位於斯德哥爾摩的公寓,並開啟了長達數個月的「裝修過程」。然而,在新居落成、親友們爭相祝賀之時,Jansson才揭露,所有照片全都是以3D建模製成,而這一切鋪陳皆是為了2023斯德哥爾摩家具展(Stockholm Furniture Fair)所策劃的社會實驗「Uncanny Spaces」。

由真實堆疊出的虛幻
「要讓謊言變得可信,其中必須摻雜真實」——這些圖片為何能以假亂真?這句話下了一個不錯的註解。Jansson巧妙地運用了生活中真實存在的事物,來為建模賦予現實的重量,其中包括IKEA紙袋、本人的外套及書籍收藏,以及各式各樣實際存在的傢俱,如他親自設計的「Marshmallow Table」、出自瑞典設計師Axel Einar Hjorth的古董桌「Lovö Dining Table」,以及義大利設計師Ettore Sottsass的粉色波浪鏡「Ultrafragola Mirror」。


除了內部擺設外,連空間本身也是由真正的公寓轉化而來,為力求寫實,Jansson徹底考察房屋細節,並完整還原了斑駁牆面和電線配置。


我們是否已對數位內容感到麻痺?
Jansson在設計貼文內容時,有時會刻意引導追蹤者進行互動,藉由一些挑釁行為來觀察大眾的反應,例如,他曾煞有其事地針對走廊粉刷的選色辦理了投票,以及更有甚者,假裝把珍貴的「Lovö Dining Table」古董桌漆成粉色,引來了包含詫異、難過以及支持等真實的反應。

而到了實驗的尾聲,他刻意將「翻修」的速度加快,並刻意讓畫面完美到有些古怪,藉此試探是否有人會注意到這是一組捏造的照片,但最終仍未有任何人發現異狀。如此現象,正帶出設計師想闡明的議題——氾濫的影像資訊是否削弱你我對真實體驗的感知?

從社群焦慮中解放
我們每天都被大量的資訊所沖刷,尤其在視覺當道的潮流中,社群充斥著各式精心編排的影像內容,人們在耳濡目染下,價值觀難免受其影響,而現實的落差就會進一步造成焦慮。

透過「Uncanny Spaces」,除了帶出資訊麻痺、社群焦慮的議題外,同時也對許多空間設計僅著重視覺效果、而忽略實際功能的陋習提出批判,Jansson認為,那些過於矯作的圖片,容易使大眾為生活設立太高的標準,隨之而來的壓力,反倒犧牲了可貴的現實體驗。

有趣的是,在斯德哥爾摩家具展舉辦期間,Jansson將「Uncanny Spaces」的3D建模扁平化後製成了木雕裝置,並展示於現場,將那間不存在的公寓帶到了現實世界中。
若好奇完整的實驗過程,可至Instagram帳號@heleneborgsgatan46一探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