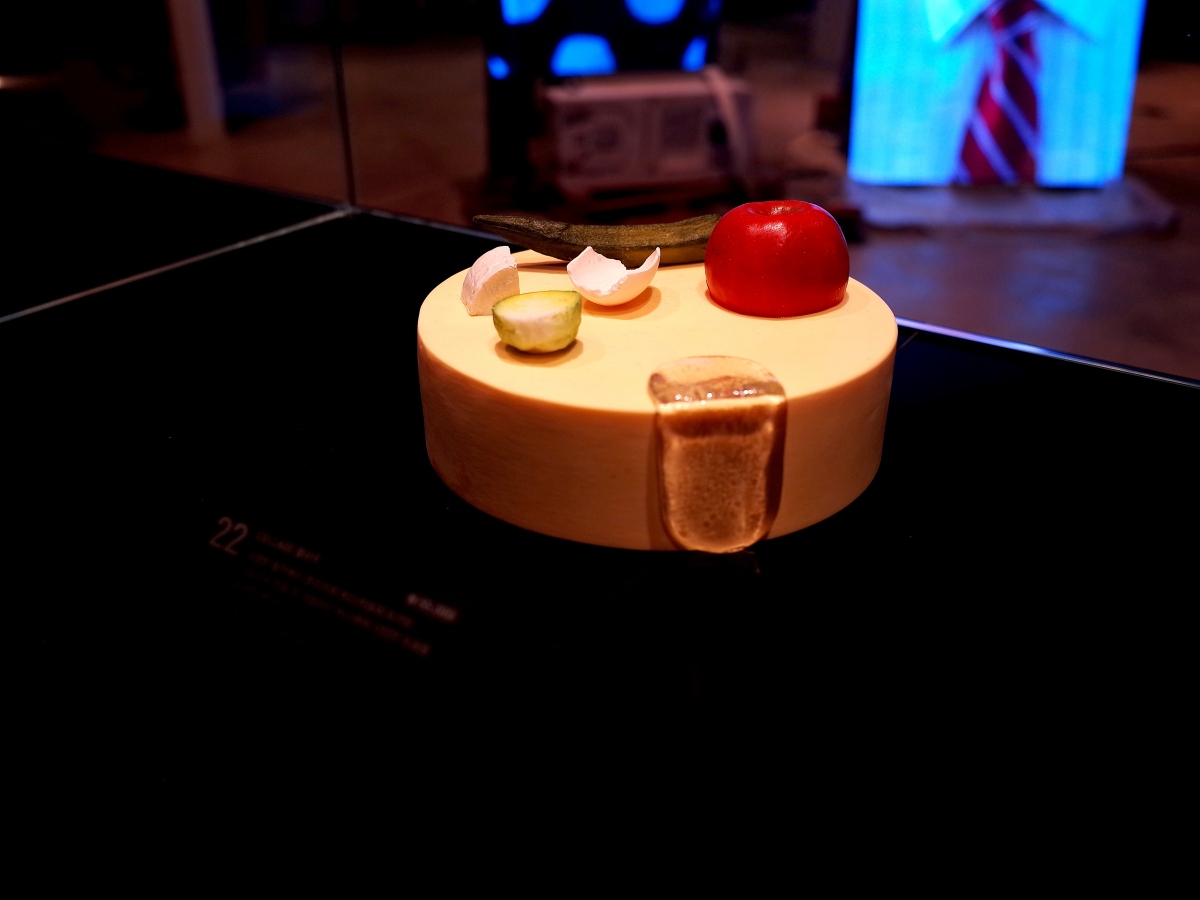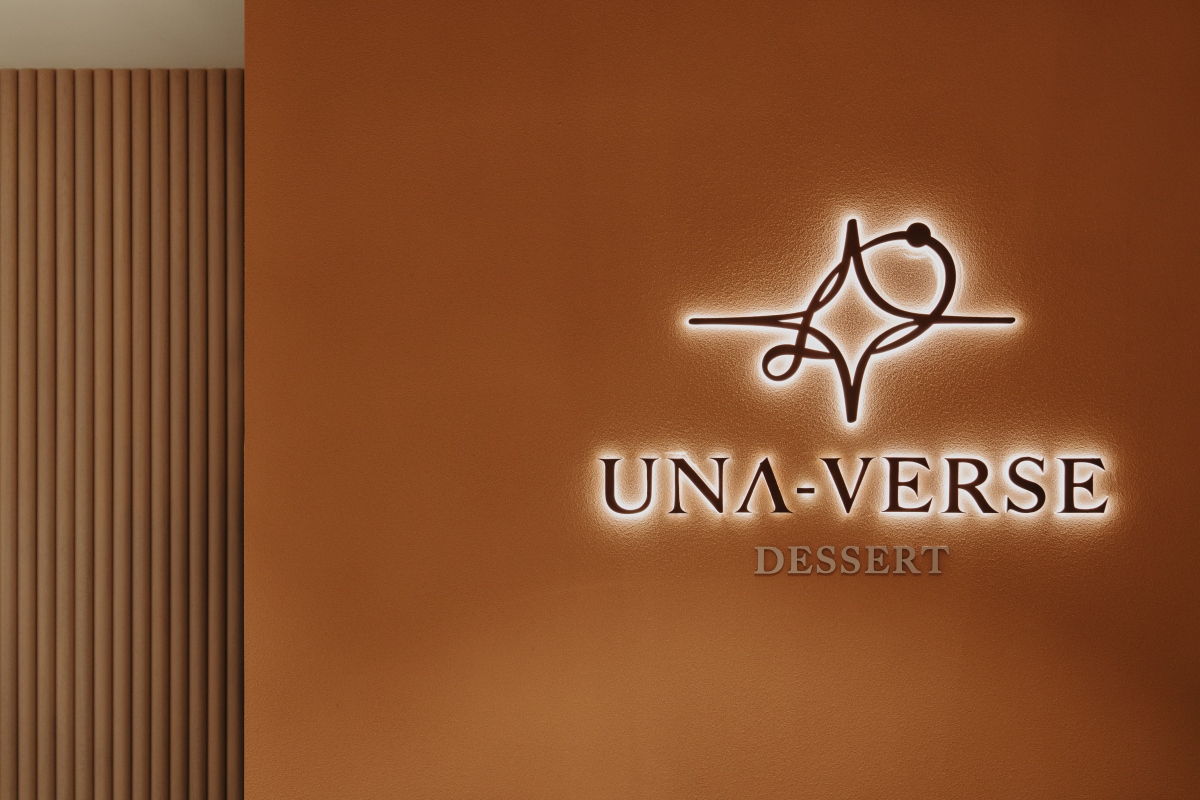1608年5月14日,年約30歲的湯瑪斯.科爾亞(Thomas Coryate)特終於厭倦了自己在倫敦的生活。他生於桑默塞特,父親是一名牧師。受過良好教育的他,平時總是和威爾斯親王亨利身邊的名人雅士聚在一起。然而,儘管他自認為是一名知識份子,與他同時代的人卻只將他看作是一個怪人;儘管他覺得倫敦的生活輕浮無趣,其他人卻認為他只是個鄉下的土包子。他在談話中經常分享異地的有趣見聞,卻沒人將這些故事當作一回事,反而還嘲笑他。在宮廷生活之外還有更廣大的世界,但卻沒人有興趣探究,除了他以外。
於是,某個春天早晨,科爾亞特坐上船前往法國,展開了環遊歐洲之旅。這趟旅程中,他幾乎都是步行。返回英格蘭後,他將磨損破爛的鞋子掛在家鄉歐德康柏(Odcombe)的教區教會裡。直到18 世紀初,那雙鞋還在那裡安息許多年。見證這趟旅程的除了他的鞋子之外,還有一本由他詳細記錄下來的遊記。這本書於1611 年出版,書名十分貼切,就叫《難以理解之見聞》。他在書中記述了兩項在義大利觀察到的新發現,日後皆對他的英國同胞帶來巨大影響。
第一項發現是在倫巴底(Lombardy)的克里蒙納(Cremona)小鎮。科爾亞特看到當地人使用一種工具,能夠「在身上產生陰影,使他們得以躲避炙熱的陽光」, 「義大利人稱這種工具為雨傘」。他描述雨傘「以皮革製成,呈小頂篷狀,內部以多個小型木製圓圈環繞,使雨傘的遮蔽範圍能擴大」。他注意到騎馬的人經常會使用這種工具,「在身上投射出長長的陰影,使他們的上半身能免於日曬」。
幾乎可預料,當科爾亞特和英國宮廷中的同僚分享這項新發現時,換來的只有嘲笑與「荒謬」等評語。不過在那之後於英國居住或旅遊的人,顯然都應該為了這項發現而對他滿懷感激,儘管雨傘在英國主要用來遮蔽連綿不斷的雨,而不是炎熱的太陽。
他的第二項偉大發現是在都靈(Turin)之旅。這趟旅程一開始就不太順遂。「很抱歉,對於這座繁榮美麗的城市,我沒辦法描述太多。」他這麼寫道,原因是他突然生病,因為「喝了皮埃蒙特(Piedmont)的甜葡萄酒⋯⋯沒有心情在街上漫遊」。接著,他還對自己的同胞提出忠告,只可惜數個世紀以來似乎都沒人理會。「我奉勸所有計劃到義大利旅行的英國人,來到這個國家後,記得一定要在葡萄酒裡加水,否則後果會不堪設想。」
從宿醉中恢復後,科爾亞特提到他的發現:「據我觀察,我所經過的義大利城鎮都有一項共通習俗。這項器具除了義大利以外,我從未在其他國家見識過,也不認為其他基督教國家會使用。」接著他開始敘述自己與叉子的奇遇,除了本章開頭引述的內容外,他也提到,用餐時若不使用叉子,而直接用手指碰觸食物,「會冒犯同桌的人,因為這麼做違反禮儀,就算無人斥責,至少也會引來旁人怒視」。
由於科爾亞特對這項發現大感驚奇,他甚至還帶了一支叉子上路,伴隨他繼續在德國旅行,最後回到英國。據他所述,他的朋友不僅嘲笑他的古怪新發現,還替他取了綽號叫「弗瑟佛」(Fucifer),意思就是「乾草叉」。對英國人來說,叉子過於矯揉做作,而義大利人會使用叉子,這點正好符合英國人對他們的觀感,像是某位當代的英國人甚至形容他們是「娘娘腔」。
科爾亞特或許是將叉子介紹給少數英國紳士的第一人,但在他之前,就已經有人在著作中提及這項器具。一個世紀前,叉子就已經正式出現在文獻中了。1526 年, 義大利作家兼編輯艾斯塔奇歐.薩雷布里諾(Estachio Celebrino)發行了他的著作《宴會餐桌擺設指南》。在詳細說明如何擺設餐桌時,他提到一片麵包、一塊餅乾、一些蛋糕,以及置於盤側的一支刀子和一支叉子。
他將叉子稱為pirone,也就是「餐叉」的意思,並表示每一張精心擺設的餐桌上都應該要有這項器具。薩雷布里諾的貢獻良多,曾出版多本與居家生活有關的指南手冊。若生於現代,他應該會是一位全方位的專題作家,因為他的寫作主題十分廣泛,包括養生食譜和梅毒療法─後者是根據自身經驗所寫,不過在此就不多加敘述了。他也曾出版一本名為《女性變美秘訣》的教戰手冊,以及一本如何預防瘟疫的書。
薩雷布里諾在威尼斯出版自己的著作,當時的威尼斯正是歐洲的出版業重心。他看起來企圖躋身全方位領域,從商業到藝術,應有盡有。在來到威尼斯之前,他除了經常出沒於賭場和妓院之外,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法庭上也時常能見到他的身影。由於他在過去曾觸犯法律,因此經常為了躲避追緝而逃亡,甚至隱姓埋名。
然而,不管他的過去多麼不光彩,他還是懂得如何使用叉子。他在書中提到叉子在正式餐宴中的使用方式,顯示出,富裕的義大利人已開始將餐桌禮儀視為文明的象徵。爾後,叉子也出現在畫家雅各布.巴沙諾(Jacopo Bassano)的《最後的晚餐》中。那是他於1542 年發表的著名作品,也是第一個描繪出叉子的畫作。儘管畫中,坐在耶穌身旁的人個個肌肉發達、體態健美,很容易使欣賞畫作的人分心,然而,在耶穌右側、一臉白鬚的門徒彼得(Peter),手中的兩刺餐叉仍舊清晰可見。
叉子當時在英國還是沒有流行起來。美國食物歷史學家克里弗德.A.萊特(Clifford A. Wright)認為,這或許是因為「叉子並不實用,僅能用來展現禮儀; 實際用餐時,只要有手指、刀子和湯匙就夠了。叉子這項發明之所以問世,是因為居住於城市中的某一階級人士對於『好品味』有了新的體悟,這也是『中產階級』(bourgeois)一詞原本的涵義」。
從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所展示的一套早期餐具中可見,刀叉長久以來都是優雅與財富的象徵。這套華麗的法國製餐具源自16 世紀,皮革製的外箱裡包含刀子、叉子和肉叉。若是在朋友面前拿出這套餐具,想必會令對方稱羨不已。雖然這個時期的叉子十分稀有,但刀子很普遍。流傳至今的刀子當中有許多狀態仍十分良好,也許我們可以猜測當時的人也很少使用刀子,他們還是比較喜歡用手抓食物。
回溯到遠古時期,更早的文獻也有叉子的蹤跡。除了古埃及神廟會利用大型串叉將獻祭品舉起外,中東宮廷早在7 世紀就開始使用小型的兩刺叉。史料記載中也可發現,11 世紀拜占庭公主曾使用這項器具。這位來自希臘的公主嫁給了一位威尼斯總督。她被人瞧見手中握著一支叉子,結果遭威尼斯的神職人員嚴厲斥責,認為她違逆上帝要人使用手指的旨意。目睹她使用叉子的人也認為這種行為極為惡劣。「她溺於享受,不願委屈自己用手觸碰食物」,「命令宦官將食物切成小塊,然後再用一種兩刺的金製器具,將食物送入口中」。
接下來的數百年內,叉子似乎銷聲匿跡,直到薩雷布里諾的著作出版後,才又出現在英國的歷史中。但還要再等上一段時間,叉子才開始普及。凱薩琳.德.麥地奇於1533 年嫁給法國的亨利二世,當時她的嫁妝裡包含數十支叉子, 皆由知名的義大利鐵匠所製。不過叉子在當時沒有流行起來。法國人認為叉子很危險,德國牧師與神學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甚至擔心叉子會動搖他的新教信仰。「上帝庇護我,使我不受叉子威脅。」他曾這麼說。
於是,科爾亞特的英國同胞繼續用手撕肉再塞進嘴裡。直到一百年後,英王查理一世於1633 年宣布「使用叉子是合乎禮儀的行為」,叉子才在社會各個階層逐漸流傳。
歷史上性情古怪的作家似乎較偏好在著作中提到叉子。喬治.席特維爾爵士是20世紀初的荒誕作家,也是詩人艾迪特.席特維爾(Edith Sitwell)的父親。他發表了大量著作,其中較特別的除了《多聲部合唱的起源》、《中世紀含鉛珠寶的裝飾圖案設計》與《將孔雀引進西方庭園》,還有《叉子的歷史》(The History of Fork)。
可惜的是,喬治爵士的大作並沒有留存下來。某些人認為這些作品全是他兒子奧斯伯特捏造出來的,畢竟,奧斯伯特後來就是靠著寫文章諷刺老爸而闖出名堂。這樣的揣測似乎也很合理,因為喬治爵士在寫作之餘,都將時間投注在自己的「有用」發明上,例如用來消滅黃蜂的左輪手槍。
科爾亞特和席特維爾都因為自己對叉子深感興趣而遭世人恥笑。僅管他們在旁人眼中都是怪人,他們至少都察覺出,這項已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具--叉子,其卓越與不凡的意義。
更多有趣的料理文化史,都在La Vie麥浩斯出版的《料理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