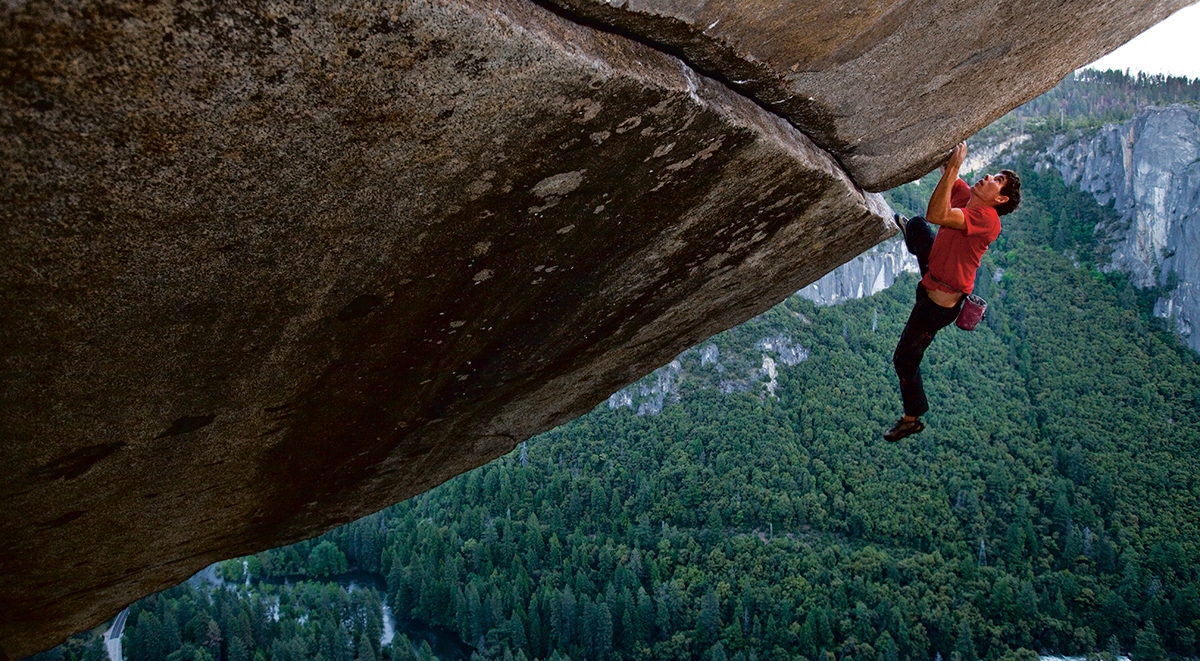2022年6月16日「世界海龜日」,風潮唱片推出由金獎自然音樂製作人吳金黛發行的生態紀實MV「洋流裡的飛翔」,團隊前往小琉球拍攝海龜生存環境、素材橫跨2019至2022年,最特別的是,整支MV是以iPhone拍攝而成。除了透過影片讓大家一同關注海龜生存環境、重視生態保育,負責MV拍攝的生態攝影師黃一峯與李維娜,還要告訴大家,使用iPhone拍攝水底美景最實用的4個小技巧。

1. 不要使用防水袋
想要進行水中拍攝,最好別用防水袋。防水袋的防水係數不夠,上岸後多少會發現袋裡還殘留水氣,即使手機防水,「海水的鹽分具有腐蝕性,對金屬元件很傷。」
。首選「金屬」防水殼,黃一峯與李維娜折衷選擇塑膠防水殼
。具備「物理按鍵」下水後操作會更順手
。可抽「真空」防水殼,確保手機不會浸水
黃一峯建議「最好提早一週把防水裝備買好,在家事先測試熟悉器材,我們本來就不是在水中生活的動物,一下水難免慌張,拍攝的困難度也會倍增。」
避免防水殼起霧的小技巧:使用金屬防水殼還有一個好處是「不會起霧」,「我們現在用的塑料殼,最麻煩的是只要有水氣就會起霧。」他們的解決方法是,出門前先用「除濕機」確保防水殼乾燥。

2. 練習手持穩定性
水中攝影無法為iPhone加裝手持穩定器,即使iPhone防抖性能不錯,但面對海流與海浪,對拍攝都是一大考驗,非得加強手持穩定性,李維娜也很老實的說「真的沒有什麼技巧,除了練習、還是練習。」如果相機拿不好,拍不到好畫面、手滑器材受損,還會因為動作太大破壞海洋生物、踢到珊瑚礁等問題「我們浮淺了60-70次之後,才敢拿器材下去拍攝,在浪區雖然光線好,但常會遇到2-3米大浪,一定要學會保護自己、器材和海洋生物們。」
3. 淺水處光線充足
水中攝影,最怕的就是「光線」問題,MV很多鏡頭都在浪區,亮度夠,不需要另外加燈就可以拍到不錯的畫面,李維娜總結:「水深5米以上,都可以不用加燈,淺水處還能捕捉波光淋漓的自然光。」


4. 開啟HDR擷取更多動態範圍
黃一峯和李維娜因為拍攝專業影片,會在ProRes模式拍攝,但缺點是很佔手機空間,李維娜建議,「影片格式調整在4K/30 fps、1080p HD/60 fps就很夠用,最好再把HDR打開,拍攝動態範圍更廣,多數影像剪輯軟體也支援HDR格式。」黃一峯補充「我習慣在iPhone內建編輯裡,先選擇需要的片段,再送到影像剪輯軟體編輯,整個工作速度會快很多。」
iPhone水中攝影的優勢?
李維娜說「GoPro體積比iPhone更小,但光線百分百充足才能有比較好的成像,最近拍攝距離也有限,iPhone可以變焦,不用靠近也能拍得很清楚,我們還會把它架在礁岩間、放在地上,拍攝害羞、怕人的海洋生物,我覺得它的水中攝影能力,在體積和性能間求取平衡的CP值很高。」

拍攝最困擾的是iPhone殼不支援觸控
黃一峯與李維娜使用iPhone拍攝,遇到最大的困擾是防水殼無法觸控螢幕「嚴格的說不是iPhone的問題,而是搭配器材沒有支援,無法觸控螢幕,下水後就無法控制對焦點。」他們建議專業工作者,可把iPhone當做備用機,黃一峯「它即使裝上防水殼,體積還是很小,我習慣放在衣服口袋,大相機有狀況,馬上可以用iPhone支援。」主要還是因為水中拍攝工作困難「下水後,想上岸還得考慮減壓問題,很麻煩,拍攝時,我們必須一直克服機器可能發生的各種狀況,機器越聰明、工作就越省力,iPhone下水後穩定性很好,對焦點也不會亂跑,這是使用上的一大優勢。」


從iPhone XS拍到iPhone 13最有感的差異是什麼?
「洋流裡的飛翔」MV集結2019到2022年水中攝影的片段,黃一峯回憶「對焦」的清晰度,真的差很多,影片中有一段海龜露出水面換氣再潛入水中的片段的連續動作,都能準確對焦;畫質像素提升也非常顯著,「螢幕亮度提升」在拍攝時真的很方便,「浮淺時很容易看不清楚螢幕,專業攝影機會搭配監視螢幕,iPhone尺寸和監視螢幕差不多,拍攝時監看或回看都變得很直覺。」

長時間透過鏡頭觀察自然環境的黃一峯和李維娜,對環境改變特別有感,「因為海洋污染、氣候暖化造成的珊瑚礁白化問題,已經有很多志工為海洋努力,小琉球有專門撿拾廢棄物的志工隊、也有復育珊瑚團隊,但我認為,關注這些議題時,不要只看到悲傷的一面,也要把美的部分傳遞給大家。」他們和「海龜點點名」合作,這個團隊是由(素人)公民科學家組成,他們熱愛潛水,在水中拍攝到的海龜,可以送到海龜點點名資料庫,這也是我們可以為海龜做的事之一,「例如透過素人科學家的眼睛,建立亞洲綠蠵龜名錄後,就可以解開牠們產卵、覓食、休息地點,更積極的幫助牠們自在的在海洋生活。」
水中攝影不只是有趣而已,還可以積極地為生態、為環境、為海洋做更多事。
圖片提供|黃一峯、李維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