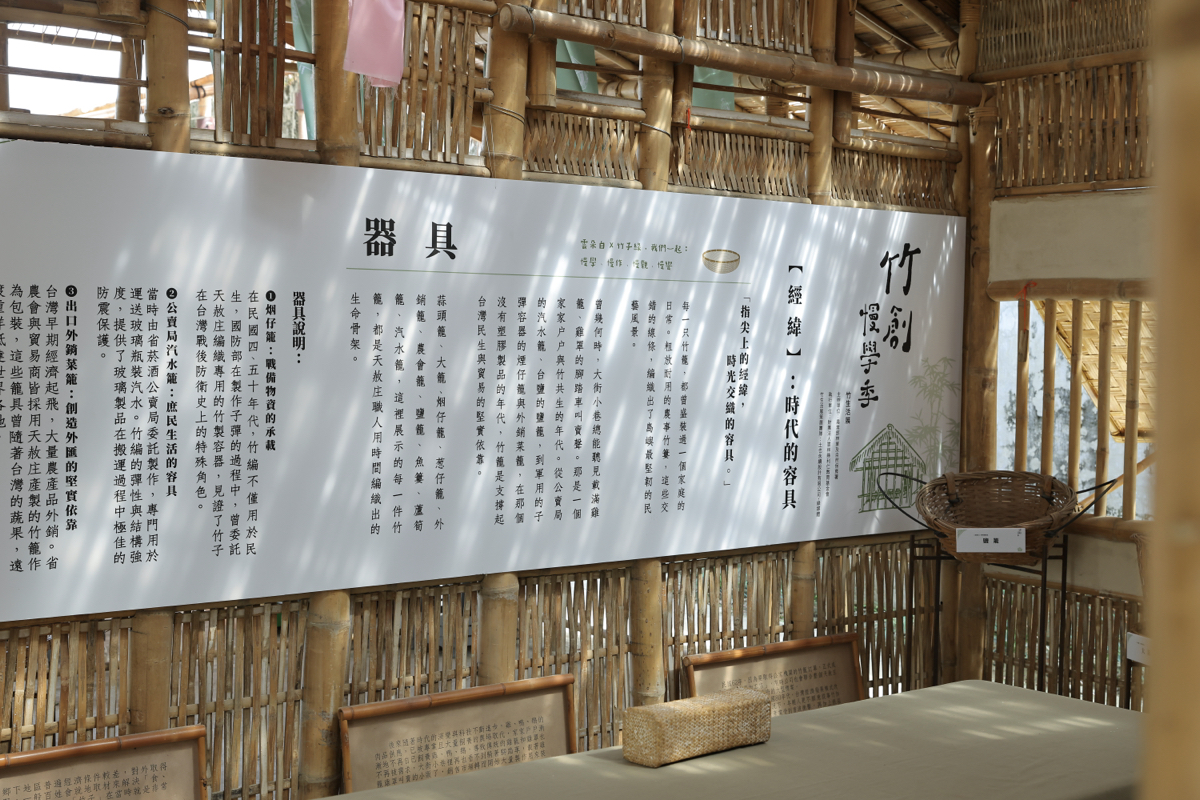就地取材、安居落戶,「自然」是建築理論中最古老的概念之一,當看到「無礦」以山林煤礦遺構僻一處人類與自己安然共處的洞天,也許正因其外部形態的不完整,才能和環境相互編織,和光、風、人,以及人的活動彼此融合,而自然建築不僅是設計手法,更多的是從根本上對「關係」的反思。為了讓我們在天地間詩意棲居,田中央和自然洋行各自在實驗的路上,看到了哪些未竟之可能?
過去田中央以黃聲遠為首,透過公共工程改造環境景觀,以宜蘭模式讓建築人相信每個小地方都能有自己的幸福樣貌,而現任執行長劉黃謝堯設計的「利澤飛灰暫存場」及蘇子睿設計的「台北植物園溫室整建工程」則入選2022年第6屆《ADA新銳建築展》,前者成為人們反思永續議題之處,後者製造多樣微氣候讓植物更自在舒展。
自然洋行創辦人曾志偉和夥伴高靖捷、負責營運無礦的林凡榆,藉由少少原始感覺研究室、勤美學森大、了了礁溪等作品,讓步入者能真正安頓身心,並從材料、質感、光線等維度來理解空間,時光就此緩滯了下來。
這次雙方約在三峽古礦場改造的無礦,分享為了找到「現代人的棲身之地」,彼此如何克制、反省、內探,甚至是敬畏。

Q:想請雙方先聊聊,你們心中的自然系建築,有哪些定義?
田中央 劉黃謝堯
因應人文、歷史、地理持續變動,人為了生存而尋找或創造更多方法建構環境,或觀察與回應當地的環境特質。像台灣的緯度與地理條件,有平原、高山、海岸等多樣地形,早期為了天災、防禦生存的高腳屋,抵禦颱風且冬暖夏涼的蘭嶼半穴居;或利用當地取得的塊石、樹幹、竹林等材料構築,雖然沒有現代建築慣用的穩定強度,但也提醒我們,在生存本質上,運用最低限度的構築方法一樣可行。
田中央 蘇子睿
攝影師拍照的空間構圖是一種建築,人要在山裡面生活,總要有地方可以睡覺、找一個樹幹擺出舒適的姿勢,那算不算一種建築?我不認為自己做的是自然系建築,比如台北植物園就一點也不自然,植物全都是人為種出來的,並非原始自然的風貌。同時,溫室也刻意避免去做任何模仿植物的舉動,用最簡單的方式搭建構造,一方面提供植物的生活空間,另一方面是解決植物園現有的問題。自然是「自然而然」,就每個不同的基地條件來看,建築物如何依順著並生長出來,彼此產生對應關係。
自然洋行 高靖捷
《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書中提及,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這世界沒有什麼是不自然的,只要有可能發生的事情都是自然,人為的任何事情亦為自然的一部分。道家也曾談過道法自然,所有的發生都屬於自然運行的道理,沒有任何一件事情在自然之外。對我而言,自然是很難用言語去說明的,需要透過時間慢慢體會它的面貌。
自然洋行 林凡榆
「大自然」這3個字,本身就有其危險性,而且是野心勃勃的,而人類過去是費盡力氣在與之抗衡。像無礦這裡的自然,也是需要我們去順應和對抗的,比如這間藥草室,如果沒有放除濕機,大家肯定無法感到很舒適。親近自然的前提,需要我們先願意非常透徹地理解它,理解到當需要跟它共存時,到底要犧牲和付出到什麼程度?
自然洋行 曾志偉
維基百科的定義頗為犀利,它說自然指的是天體運行裡面的任何事物,無論生物或非生物,彼此之間的關係都取決於你如何看待,或對其關注而形成意識上的變化。這麼說的話,「自然」其實是贅詞,究竟「自然」是哪一種類別的建築或設計導向,還是需要回歸到設計者、創作者本身所切入的角度會更具象。
Q:礁溪桂竹林籃球場及少少原始感覺研究室,分別是雙方在台灣的起點,請問你們對彼此作品的第一印象或記憶中較為深刻的作品是?
田中央 劉黃謝堯
第一次去少少的時候,當時剛好在辦活動,爬了一小段山路上去後,好像在有點野的山上,突然進到一個相對穩定的空間。我帶著剛學會爬的女兒去,她在裡面爬一下、停一下,再爬一下,然後慢慢地移動,那個畫面會讓我想到當時年幼、尚未被社會馴化的她,彷彿是山裡面的小動物或一株植物的種子,隨著風輕輕擺動,有一種很奇妙的感覺。

自然洋行 高靖捷
印象最深的應該是羅東文化工場,除了很多人在使用,可以看到當地居民騎腳踏車、打球、 聊天,很有生活場所感,並且讓人們能夠自在地在其中走動。尤其是工場上面那懸在半空中像飛行船的構造,和從底下沿著平台的廊道步行上去,忽然有一種類似在爬山的感覺,登高望遠後好好呼吸,相當心曠神怡。

Q:志偉曾提問業主:「你能不能接受被大自然打擾?」而雲門劇場的完工期限從原本的半年、1年,到7年的時間,是少數「使用的比想像的好」,你們如何看待這樣的未知性、適應性,及可能產生的落差?
自然洋行 曾志偉
大自然始終是個謎,為什麼幾千年、幾萬年下來,大家對大自然的共情會超越建築?它是深不可測的。若從設計角度來談,我還是建議原來有人居的地方盡量聚集、自然環境則盡量降低干擾。
這問題本質上是人的慾望,既要在自然裡面又要有生活,那個擺盪是很矛盾的,想像一下坐在家裡,放眼看窗外有一大片自然風景,還要有一些野兔從面前跑過去等等,其實是用視覺和慾望在消耗自然。反而鄰著自然而住,需要的時候走近、突破結界再回來,比較不會失去萬物共生的狀態。

田中央 劉黃謝堯
雲門確實是少數用途及功能上非常明確的例子,其他像羅東文化工場、樟仔園,滿多是大家不斷想像怎麼用,同時在都市或整體環境中留下建築空白,由無法預期的事情來填充,包括爸媽陪小朋友學走路、國小騎單車買冰來這裡吃,與同學相約來聊天看展覽,自然而然就圍繞著生活。
另外像關埔國小,學校老師有向我們反應希望打造更多學童能探索的空間,有別於以往為了管理方便,讓每個空間都一目了然,校園有些小角落是設計給同學之間互動的,如同他們自己在鄰里間玩耍會找到一些祕密基地,不被預期的小小空間裡,孩子們的創意正在萌生中。

Q:雙方在選擇材料上,如纖維紙漿皮層、網室透氣系統、組裝角鋼等,在虛實和輕重之間有什麼標準?
田中央 蘇子睿
壯圍沙丘是我進田中央的第一個案子,人類要在那種條件下,有個可以遮風蔽雨的環境,又要方便營運團隊日後維護跟營運,最簡單的大概就是抗鹽分的混凝土。
台北植物園的概念跟丟丟噹森林公園有點像,由於不知道那塊地以後會變怎麼樣,為了大家著想,想辦法先把那個空間占住,同時也想突顯樹冠層讓大眾看到,很多大喬木都已經被保護在植物園裡面,不只有花花草草,所以必須要高到大概10公尺左右,用木構或混凝土顯然都不是太聰明、經濟的作法,最後選讓建築比較消失在環境裡面的鋼構。
如今強調要減碳、要減少材料,相對要付出更多人力成本,比如無礦內這些老件或修復工作,其實一點也不便宜,這也是值得思考的。

自然洋行 高靖捷
洋行主要著重在捕捉一個整體意象,把對自然的感受性,反映於空間的設計之中,比如在做少少原始感覺研究室時,反覆嘗試的過程中,發現溫室遮光網除了能滿足台灣常民意 象,更重要的是放上去之後,最適合描述我們對於原始感覺的想像,因此往往「自然」的發生或出現,並沒有藉由太多言語主導,而是透過身體最直觀的共鳴,讓它自然而然發生。
Q:自然洋行過去盡量留下文明世界裡「無用的空間」,田中央面對大量體的建築,以碎化或減化來降低對環境的衝擊,在與環境共生的框架下,雙方各有哪些警覺和在意?
田中央 蘇子睿
以大棚架為例,下面並無遊樂設施,可是只要能遮雨、遮陽、呼吸戶外空氣,大眾就會自動聚集過來。黃聲遠老師傳達給我們的幾個觀念,一個是設計怎麼改都可以,只要竭盡可能把公共性做到最大,此外,其他因素隨時都在變。 還有個人特質很重要,像我自己是想比較多的一個人,老師偶爾會提醒我不要因為顧慮外界而失去個人特質。
田中央沒有案子是只屬於某個人的,而是共同完成,同事路過彼此的模型,都可以發表意見,或內心有疑問的時候,就把老師找來問問他的想法。羅東文化二館從設計到完成歷經10幾年,完工後還有很多其他計畫停擺,羅東是一個很適合散步的城市,但到現在我們還是看到很多只有兩線道的巷弄,老人家為了買東西騎著摩托車在裡面穿梭,令人感到驚險萬分。
田中央 劉黃謝堯
能小就小,能不蓋就不蓋吧!或是蓋了像是原本就在那邊很久的樣子。前面提到的新竹關埔國小,周圍都是密集的大樓實體建築,國小反而把建築壓得很低矮,與新種樹林、地形創造出縫隙,教室單元每個像是樹冠尺寸,多重交錯的植物與建築空間,彷彿小矮人的家,在樹林聚落中穿來穿去,樹越長越大,越不會注意到建築。

自然洋行 林凡榆
若從上帝視角看,所謂都市跟自然的邊界,時常感到非常無力,最終要回歸到擁有資本的一方才能推進,而非推廣自然生活有多美好就能改變,付出的勞力代價更不成正比。
無礦做更多的是放平到落地視角,走路時看不到對面的三峽河,面對的是眼前的雜草和垃圾,還有當下進入的客人,降到動物那種很低矮、很渺小, 只有一點點力量可以做事。生活太快,我們常沒辦法好好思考一天裡面做的每個決定是不是發自內心,希望空間讓人們的大腦緩下來,恢復身體真實的感覺。

Q:以台灣的自然、氣候、地理等條件而言,你們理想的自然系建築可能是什麼模樣?
田中央 劉黃謝堯
自然系建築某種程度可說是新陳代謝的概念,使大眾改變認知,建築完成後不會長久不壞,既使是鋼筋混凝土在常地震的台灣,幾年後多少必會產生裂縫,使用者可一般性地維護和照顧,才能延長建築生命。
以我熟悉的宜蘭來說,因長年多雨,住家或公共空可增加半戶外雨棚的空間,讓人於雨季仍可進行戶外活動,不用長時間困於室內,同時降低設備使用的能源消耗,達成微自然的建築空間。
田中央 蘇子睿
我想到多數人喜歡宜蘭的原因,無非是因為冬天休耕期時,宜蘭的天空、水田跟山巒倒映的景色,讓大家一出雪隧後就很感動,但當農舍越來越多的時候,這些東西慢慢不見了,人們自己破壞了原本很珍惜的景觀。所以我還滿同意曾志偉老師前面所提及,往集村式的集合住宅社區發展,水田則繼續維持原本樣貌。
自然洋行 曾志偉
我認為這是人類集體意識的「善意」和「慾念」之間的權衡。我們從小被養成的過程中,有自卑、有自信、有慾望、有挑剔,有很多複雜的成因,形塑出這個島嶼的人民,卻往往無法聚焦共識。如果有一些空間的設計,可以給予「小我化」的寧靜,導向更低度的慾望,而避免娛樂化導致建築最終走向不可收拾之地步,也是自然系建築的一種可能性,委託部分自然力量加上人為力量,進而得到沉澱,讓人們更謹慎並減緩開發的速度。



自然洋行建築事務所
由建築師曾志偉成立於2003年,工作室位於台北外雙溪陽明山國家公園後山,主要設計思考著重於建築、景觀、環境、感知、策展等創意設計的工作團隊,並專注於手工美學及尊重自然之感性,作品包括歷史建築物改造、新型態研究機構及部分實驗性住宅、飯店等,並持續探索輕質、異材質構造及其運用可能性。
田中央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由建築師黃聲遠成立於1994年,嘗試創造能跟宜蘭地方生活和環境相融合的建築實踐,由百位以上歷代夥伴組成穩定成 長且逐漸舒張開來的「意志同盟」,持續探索真實本質,同時作為居民和專業工作者,他們如藤蔓莖脈葡爬於小鎮與鄉野,不急於給出答案,運用想像力蔓延、連結、開放,長出枝節,拓展更多的空間契機。
採訪整理|張瑋涵
攝影|林科呈
圖片提供|田中央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自然洋行建築事務所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 La Vie 2024/3月號《建築自然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