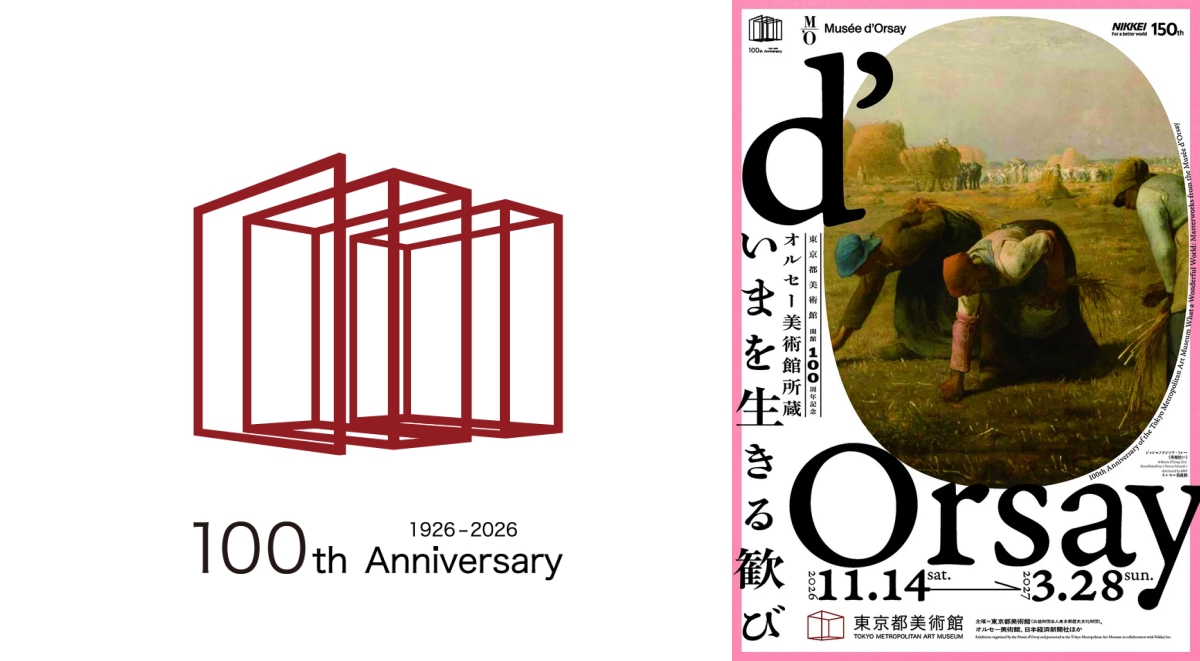2011年,西班牙塞爾維亞廣場撐起了一把偌大的都市磨菇傘(Metropol Parasol),這個全球最大的木製結構建築,打開了西班牙的建築新貌,也終於讓全世界注意到這位德國當代建築明星―Jürgen Mayer H。
Jürgen Mayer H曾就讀於斯圖加特大學、庫柏聯合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作品受邀於世界各地展出,並獲紐約和舊金山MoMA收藏。2008年時,獲德國《明鏡周刊》選為天才接班人,是繼包浩斯創辦人沃爾特‧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以及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之後,德國建築界的耀眼新星。建築作品從丹麥、波蘭、西班牙到比利時,每每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共建築作品。德國Ostfildern鎮會堂、卡爾斯魯厄大學學生中心、西班牙塞爾維亞的都市磨菇傘、S11辦公室、Home.Haus孤兒院等作品,均迥異於過往德國建築予人的印象,而擁有鮮明如簽名般的風格,常被稱為「液化的建築」,他則以「Beyond the Blob」來形容這取自於化學的概念。
其建築作品經常有著膨脹或曲折的外觀,窗口如同蜂窩又像是突出的眼睛,彷彿來自未來的建築, 抹去了稜角,而讓所有元素融為一體。「我們希望每個建築作品提供不只一個解讀潛力,不過自然與科技之間的關係始終是潛在的主題。」富有創新精神的他,敢思敢為,經常跨領域創作,包含建築、設計以及藝術,他關注建築、交流以及新科技三方面的交互運用,持續探索人類、技術與自然型態之間的關係。
「我們渴望擁有可以嘗試的空間,並希望能透過建築帶出所在地的種種潛力與可能性,這往往在一開始時讓人覺得有點冒險,但我們所有的項目,目前為止都已證明是經濟的、可能的。」Mayer表示,他們總是設法找到能夠分享其認為建築是一種冒險的客戶。
Jürgen Mayer H.趕上了時代變動。新建築材料的探索催生了不同建築形式的可能;網路及科技則為人們與自然、建築之間的關係,帶來新的想像;同時,建築師開始跨越國界,作品誕生於世界各地。他認為建築並非一種孤立的追求,其完成依賴客戶端、工程師、建築師良好的合作關係,同時建築也應將城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連接起來。種種條件變化與不同文化之間彼此激盪,令建築存有許多表現可能,而Mayer則以意義的模糊性為策略,讓這時代的多元、曖昧特性,潛藏於建築之中,藉著液化的建築,賦予個人解讀的多重可能。
Info│Jürgen Mayer H.
1996年成立跨領域的J.Mayer H.事務所,從事包含城市規劃、裝置及新材料研究等,被譽為德國繼包浩斯創辦人沃爾特‧格羅佩斯及密斯凡德羅之後的建築界明星,榮獲2003年密斯凡德羅獎、2005年Holcim獎銅獎及2010年奧迪未來城市高峰論壇的可持續建築獎。
Text / La Vie編輯群
Photo / J.MAYER.H、yatzer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 2014《La Vie》雜誌 4 月號】